撰文|吴俊燊 董牧孜
9月2日,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颇有影响力的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威尼斯的医院离世,享年59岁。格雷伯的妻子妮卡·杜布罗夫斯基(Nika Dubrovsky)于9月3日上午证实了他的死讯。杜布罗夫斯基在推特上说:“昨天,全世界最好的人、我的丈夫和挚友大卫·格雷伯,在威尼斯的一家医院里离开了人世。”死因尚不明确。直到去世前一天,格雷伯还一直活跃在推特上。
格雷伯的父母是自学成才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他的母亲曾是一名制衣工人,父亲参加了巴塞罗那的西班牙大革命并参与了西班牙内战。格雷伯在被描述为“充满激进政治”的公寓楼里长大,根据他在2005年的采访,格雷伯从16岁起就一直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

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
格雷伯对学术的兴趣始于青少年时期,那时他就开始翻译玛雅象形文字。他曾在纽约州立大学学习采购学,1996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之后,他获得了著名的富布赖特奖学金(Fulbright fellowship),并花了两年时间在马达加斯加进行人类学实地考察。
格雷伯的第一份教学工作是在哈弗福德学院担任人类学助理教授。1998年,他开始在耶鲁大学担任副教授。2005年,在他即将获得耶鲁大学终身教职的前一年,学校决定不与他续约,格雷伯怀疑这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当时,有4500多名同事和学生在支持他的请愿书上签了名,耶鲁大学转而向他提供了一年的带薪休假。2015年,他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我想我有两个弱点。第一,我似乎太喜欢我的工作了;其次,我来自错误的社会阶级——工人阶级。”
1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关键人物:
“我们是99% ”
20世纪90年代后期,格雷伯开始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他是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关键人物。
2011年11月,《滚石》杂志称赞格雷伯为占领华尔街运动提供了主题:“我们是99% ”,尽管格雷伯在《民主项目》中写道,这个口号“是集体创造的”。格雷伯于8月2日帮助创立了第一届纽约市大会,只有60名参与者。他在接下来的六个星期中参与了迅速发展的运动,包括协助大会,参加工作组会议以及组织有关非暴力抵抗的法律和医学培训和培训班。在Zuccotti公园扎营几天后,他离开纽约前往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
格雷伯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缺乏对现有政治机构或法律结构合法性的认识,对非等级共识决策和前途政治的拥护使其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项目。与阿拉伯之春相比,格雷伯声称占领华尔街和其他当代基层抗议活动代表着“关于美国帝国解体的一系列谈判的开端。”他在半岛电视台的报道中指出,占领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关于“仅对道德秩序作出回应,而不是对法律秩序作出承诺”,因此,在没有必要许可的情况下举行了会议。为了捍卫占领运动的这一早期决定,他说:“作为公众,我们不需要获得占用公共空间的许可”。
格雷伯在2014年发推文说,由于他参与了《占领华尔街》,他被驱逐出了50多年的家。他补充说,与占领有关的其他人也受到了类似的“行政骚扰”。
2019年10月11日,格雷伯在特拉法加广场的灭绝叛乱抗议活动中发表讲话。格雷伯谈到“狗屁工作”(bullshit job)与环境损害之间的关系,并建议环境运动应将这些工作与不必要的建筑或基础设施项目结合起来,并计划将其淘汰视为重要问题。
2015年3月接受《卫报》采访时,格雷伯将“占领华尔街”运动称为“后官僚社会的实验”。格雷伯表示,示威者希望向公众表明,人们可以在没有官僚主义的情况下履行银行的职能。他说,在抗议期间,祖科蒂公园有一个装有80万美元捐款的塑料袋,因为“占领华尔街不能有银行账户”。格雷伯说:“我总是说,行动的原则是坚持要表现得好像自己已经自由了。”
2019年11月,格里伯与其他公众人物签署了一封支持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宾(Jeremy Corbyn)的信,称他为“在民主世界多数地区与新兴的极右翼民族主义,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作斗争的希望灯塔”,并获得认可他在2019年英国大选中获胜。在2019年12月,他与其他42位主要文化人物签署了一封信,支持在2019年大选中由科宾领导的工党。信中说:“在杰里米·科宾领导下的工党选举宣言提供了一项变革性计划,该计划优先考虑人和地球的需求,而不是私人利益和少数人的既得利益。
2
“狗屁工作”理论:
反思工作的本质
大卫·格雷伯他著有多部关于官僚主义和经济学的畅销书,包括《狗屁工作:一个理论》(Bullshit Jobs: A Theory)和《债:第一个5000年》(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他的最后一本书《万物的黎明:人类新历史》(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将于2021年秋季出版,该书与大卫温罗夫(David Wengrove)合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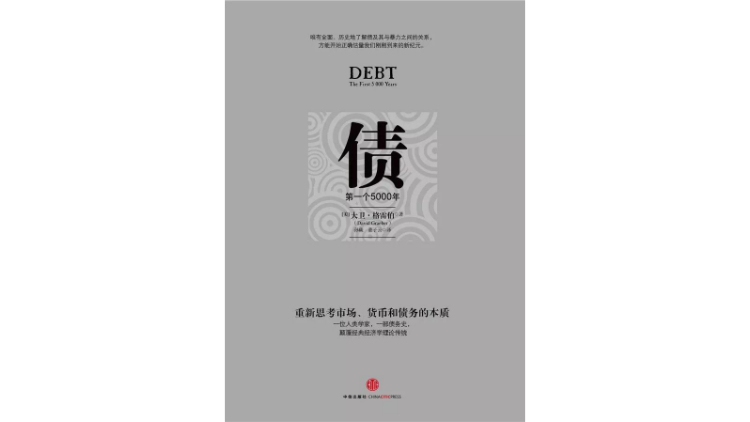 《债:第一个5000年》,[美]大卫·格雷伯 著,董子云、孙碳 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11月
《债:第一个5000年》,[美]大卫·格雷伯 著,董子云、孙碳 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11月
2013年他写过一篇戏谑的短文《论狗屁工作现象》(“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 A Work Rant”),被译成了17种语言,病毒一般传播开来。2018年,由这篇文章扩写而成的新书《狗屁工作:一种理论》(Bullshit Jobs: A Theory)出版,立即引发英文知识界的热议。这本黑色幽默的反MBA价值观畅销书,连同其他学者有关后工作、基本收入的研究,构成了我们反思这个时代工作本质的知识结构。
“地狱就是一群人都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完成一件他们不喜欢、也不太擅长的任务上。”在格雷伯看来,现代经济中的大量工作已经足以被描述为“地狱的一种可能版本”。世界上有数百万人——文员、行政人员、顾问、电话推销员、公司律师、客服等——都在毫无意义的、不必要的工作中辛苦劳作,并且他们也心知肚明。技术进步令很多人面临失业,却也创造出大量的狗屁工作以维持社会的稳定,而这种操作与金融资本主义的神秘性息息相关。于是我们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工作得更多,成了办公桌上永无止息的西西弗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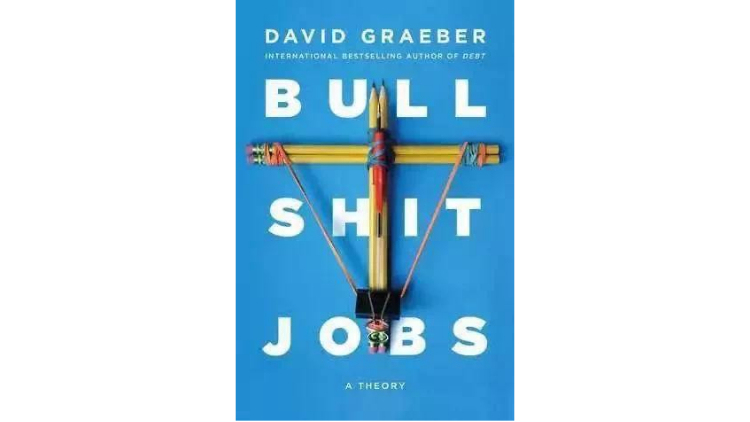 Bullshit Jobs: A Theory, David Graeber, Simon Schuster 2018.5.
Bullshit Jobs: A Theory, David Graeber, Simon Schuster 2018.5.
格雷伯在研究中发现,约有6%的人认为他们的工作毫无意义,但是依然感到快乐,这种快乐来自别的地方,比如他们在工作中会遇到喜欢的同事等等。实际上,也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准确判断自己的工作是否有用,不过人们往往倾向于说服自己相信“我的工作是有价值的”。
狗屁工作不见得是“糟糕的工作”(shit jobs),事实上,狗屁工作可能光鲜亮丽,颇受尊重,且待遇极佳。但狗屁工作缺乏的实质性的意义和贡献。假如“狗屁工作”消失的话,我们的生活不会变得更糟,甚至可能变得更好——比如那群自诩最聪明、最努力的华尔街精英,他们引以为傲的工作正是金融灾难的始作俑者。
格雷伯颇为遗憾地指出一个事实:我们的社会陷入了这样一种吊诡,你的工作对别人越有益,你工作所得的报酬反而越低,比如垃圾处理者、建筑工人、护士……于是这工作就成了一份“糟糕的工作”。格雷伯认为,“你几乎可以把‘糟糕的工作’看成是狗屁工作的反面”。
历史学家罗格斯·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称格雷伯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和杰出的作家”,而《卫报》专栏作家欧文·琼斯(Owen Jones)则称他“是一位智慧的巨人,充满人性,他的作品激励、鼓舞和教育了许多人”。工党议员约翰·麦克唐奈(John McDonnell)写道:“我把大卫视为一个非常珍贵的朋友和盟友。他打破传统的研究和写作为我们开辟了新的思维和政治激进主义的创新方法。我们都会非常想念他。”
格雷伯在企鹅兰登书屋的编辑汤姆·佩恩(Tom Penn)表示,出版社对此感到震惊,称格雷伯是“一个真正的激进分子,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先驱性的”。
佩恩说:“格雷伯鼓舞人心的工作改变并塑造了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在他的书中,他那持久的、孜孜不倦的好奇心,他那充满嘲讽而犀利的针对传统秘方的挑衅,都闪耀着光芒。最重要的是,他想象一个更美好世界的独特能力也发挥了作用,这种能力源于他深刻而持久的人性。能成为他的出版商,我们深感荣幸,我们都会想念他,想念他的善良,他的热情,他的智慧和他的友谊。他的离世所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但他留下的遗产是巨大的。他的作品和精神都将永存。”
参考链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20/sep/03/david-graeber-anthropologist-and-author-of-bullshit-jobs-dies-aged-59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吴俊燊 董牧孜;编辑:木子;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