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南方周末发表一篇名为《“不寒而栗”的爱情:北大自杀女生的聊天记录》的报道,内容引发巨大震动。北大大三女学生包丽因自杀被抢救,她的母亲从其手机中发现包丽与其男友牟某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中的内容充满精神控制和虐待,包丽的母亲认为正是这段关系造成了女儿的自杀。这段变形扭曲的关系并非真正的爱情,反而充满了恶意与羞辱,但其可怕之处正在于它的隐蔽性与欺骗性。
自南方周末报道后,一个名为“凯旋十二”的私人微信公众号发布名为《我是包丽的朋友,真相远比你知道的更可怕》长文,一方面探讨报道是否有夺人眼球的不实和不全面之处,另一方面也详细揭露和展现了包丽与男友牟某之间的聊天记录,其中充满了大量耸人听闻的言论和话语,引起人们对亲密关系中的精神控制、PUA、字母圈等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但很显然,包丽之事并非仅仅某个圈子内的小众猎奇故事。而是我们日常所见甚至许多女性经历过或是正在经历的。在包丽和男友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性别权力关系,而这一权力运作又通过他们的恋爱关系被进一步强化,并且在这其中我们也发现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被我们想象和描绘美好的亲密(爱情)关系是如何成为规训和控制的手段的,以及它对女性所具有的“谋杀”力量。
尤为需要警惕的是 ,这些关系往往“以爱之名 ”,打着爱情的旗号对“被爱的一方”进行规训甚至羞辱,我们必须洞穿事件背后的“爱情”逻辑 ,才有可能挽救下一个受害者。而在作者看来,只有首先肯定他者的独立性,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连接,才有真正的爱情生长的土壤。
撰文 | 重木
01 浪漫之爱的想象,掩盖了背后的权力问题
在德国学者尼克拉斯·卢曼的《作为激情的爱情》中,卢曼认为西方的爱情语义学自16世纪后半叶开始就出现了形式的变化,其中颇为重要的是出现在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中的“激情”之爱。它由此打破了传统骑士之爱所建构出的理想型爱情,而使得爱情走向其后的个体化和人格化,即爱情成为印证个体独立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为了爱而爱”。西方这一关于爱情的变迁在其后成为主流,并随着其19世纪的殖民风暴而开始影响被殖民地区传统的爱情观念,中国亦在其中。
在李海燕的《心灵革命》中,她通过研究近代中国在西风影响下而开始对“爱情”进行的建构和言说,展现出它与社会各个方面之间所形成的紧密联系,并且也指出了通过爱情与情感的话语来构建身份、道德、性别、权力以及国族等等。由此我们发现,近代爱情一方面在诸多新文学中成为个体解放和自由的重要媒介,但另一方面它也被更广阔的权力所收纳和整合,由此改变着它内部的建成结构与内涵。李海燕在书中提出三种模式的爱情结构,分别是儒家的、启蒙的和革命的。而伴随着革命之爱在20世纪晚期退潮,进入消费主义与流行文化中的浪漫之爱再次兴起,而渐渐成为人们对于爱情的主流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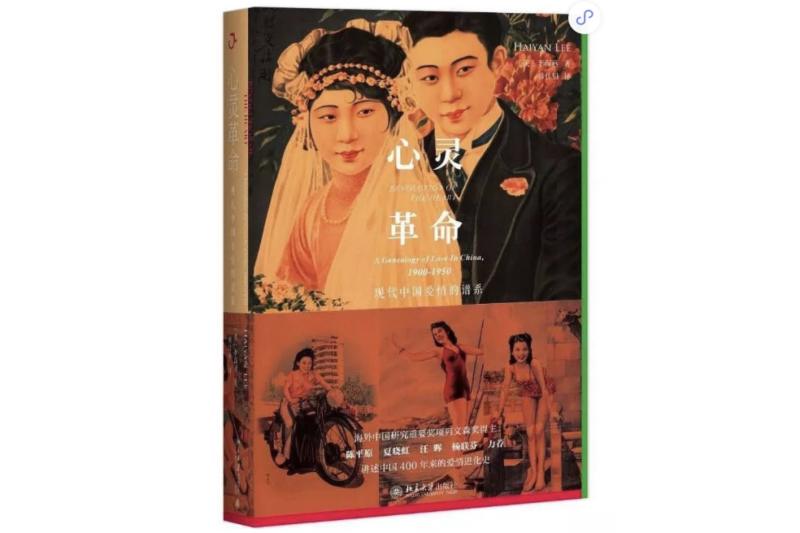
《心灵革命》
作者: [美]李海燕译者: 修佳明
版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7月
浪漫之爱的想象掩盖了爱情本身所具有的复杂以及多样性,并且这张美丽的面具还进一步地遮蔽了存在于爱情中的诸多权力问题,尤其当它涉及男女两性时。从西方中世纪的骑士之爱开始,爱情就是男性骑士用来证明自己风度、地位和权力的一个手段,因此他们所爱慕的女性对象,与其说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个体,还不如说是一个符合他想象的、遥远的魅影,永不可得。爱情和女性没什么关系,这一点虽然在其后浪漫派的爱情中有所收敛,但内部的运作机制及其意识形态却依旧占据主流。因为,在关于两性的爱情中,父权制所建构的性别制度同样被纳入其中,而当它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崛起产生联系后,它便被整合进整个现代权力体系之中。
由于传统性别权力的不平衡而导致原本建构作为两个独立个体之间平等交往的爱情也难以真正且彻底地清除其影响。并且传统对于男女两性的性别气质的建构也在爱情中被反复再生产,其中典型的诸如男性主动,女性被动;男性作为守护者,女性作为被守护者等等。这些关于两性性别制度不平衡甚至压迫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在爱情中不但未能消失,很多时候反而在“爱情神话”的保护下变得更加理所当然。
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启蒙者们,当他们提及爱情时,都与个体的自由和解放息息相关,但他们似乎都站在男性中心主义来想象和建构爱情,从而使得“爱情”充满了强烈的男权色彩;而另一方面,他们也发现爱情甚至可以作为一种投射行为,即被爱者能够成为一面镜子,爱者从中看到了自己,而未能看到作为镜子的被爱者。而在两性关系中,女性往往就处在这个位置上。
在茅盾于上世纪创作的短篇小说《创造》中,男主人公君实通过对妻子娴娴进行一系列的外貌、着装、行为和思想观念的改造,希望把她创造成一个新时代的新女性。在这里,娴娴便是作为男性君实的一面镜子出现的,就如小说中所写“他最爱的是以他的思想为思想,以他的行动为行动的夫人”,他要求娴娴“时时刻刻信仰他,看着他,听着他,摊开全灵魂来接受他的拥抱”。而君实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以爱之名。
在法国哲学家布吕克内的《爱的悖论》中,他曾研究中世纪教会在处理异教徒时的态度,即通过“以爱之名”来对他们进行规训和消灭。就连在圣奥古斯丁那里,爱也可以被用作屠杀的正当借口和手段。布吕克内指出,这种宗教式的爱最终也伴随着现代性的出现而世俗化,进入革命、政治以及私人领域。也正是在“以爱之名”下,爱者的强势彻底淹没和凌驾于被爱者的意识与存在上,甚至直接摧毁了黑格尔所设想的主奴关系。
在揭露出的包丽和牟某的聊天记录中,我们发现牟某的主动中便带着强烈的“以爱之名”来对包丽进行各种要求、索取、制约与规训。按照奥托·魏宁格在其《性与性格》一书中所指出的,这便是“男人之爱”的危险和可怖之处。
在魏宁格看来,男人之爱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般纯洁,它的目的是为了自我的完善。魏宁格指出“爱情也是一种心理投射现象,而不是一种像友谊那样的对等现象。友谊的前提是两个个体的平等;爱情则总是意味着不平等和不平衡”(2017,页271)。在爱情——或更准确地说是“男人之爱”——中,男人想象和创造着属于和符合他所欲望的女人,一旦后者出现任何偏差,便会造成前者的痛苦。因此当《创造》中娴娴的观念超越了丈夫,而让他赶紧赶上来的时候,君实的痛苦从小说一开始便出现了。而除此之外,“被冒犯的男性”所采取的另一种方法便是报复,即以他作为男性在性别制度中的权力者来对女性进行打击和伤害。在包丽事件中,当她打破了牟某对自己的想象后,牟某所采取的不正是此类恶劣手段来进行纠缠与骚扰吗?
02 父权体制如何“谋杀”了女性?
在《性与性格》中,魏宁格有一个既错误又正确的判断或许能够使我们在这里的思考更进一步。在他看来,“女人能负载他人投射给她的价值。由于女人既不行善也不作恶,她便既不抵抗也不厌恶强加在她个性上的理想。很显然,女人的道德是后天获得的,但这种道德是男人的道德,男人在追求最高爱情与奉献的过程中,将这种道德转移给了女人”。在我看来,魏宁格这段话也正揭露了父权体制和性别制度的典型运作模式,即主流性别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强制性地内置于女性意识中的,从而导致女性处于一种内部的“天人交战”状态。在爱情中,这一运作变得更为鲜明。
在关于包丽事件的报道中,都强调了包丽原本是一个性格开朗且具有主见的女生,并且对于牟某一开始在他们的爱情中所显露出的冒犯和虐待倾向提出警告,甚至提出分手。但即使包丽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她最终还是难以对抗更为强势的关于爱情的神话以及性别意识形态中的规训力量。而我们从牟某的信息中发现,他所使用的都是传统中对女性污名最典型的各种陈词滥调,如处女羞耻、贞操观念、爱情忠诚和唯一等等。这一系列污名形成一张网把包丽笼罩在其中,从而使得她失去抵抗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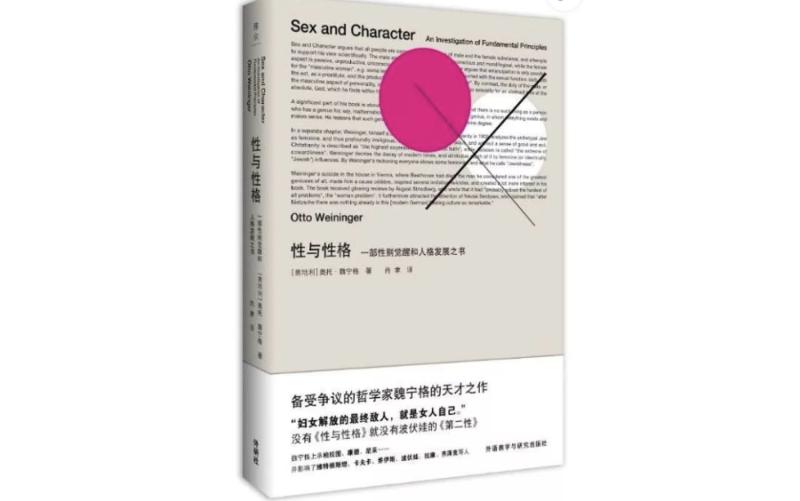
《性与性格》
作者: [奥地利]奥托·魏宁格(Otto Wengier)译者: 肖聿
版本: 雅众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7年11月
在波伏娃的《第二性》中,她再次强调了魏宁格的观点,指出“女人使男人在社会上的虚荣得以满足,还给了男人一种更为深层次的满足——他从塑造她之中得到乐趣……丈夫在性生活之外,即使是道德和头脑也支配着自己的妻子。他给她教育,在她身上打下他深深的烙印——他赋予它形式,并渗透于它们的本质之中。女人恰恰可以成为他手里的‘橡皮泥’,他可以将其任意揉搓,随心所欲地加以塑造”。牟某要求包丽称自己为“主人”,要求她在自己身上文“牟林翰的狗”,并且让人把文的整个过程录下来;除此之外,牟某还更进一步地要求包丽“为我怀一个孩子,然后去把他打掉,我留下病历单”或让包丽去“做绝育手术,然后把病历单给我”……
许多网友批评这是牟某的PUA手段,或说其只是变态,但在这背后所反映的只不过是我们日常最常见的性别不平等制度中所产生的看似极端的事件和意识形态。牟某的逻辑完全符合魏宁格和波伏娃在男人之爱和男女两性权力关系中所发现的问题。就如魏宁格所说,“男人在女人身上领悟他自己的理想,而不是领悟女人本身,这种尝试必然会摧毁女人的实际人格。因此,这种尝试对女人来说是残忍的”,到此,魏宁格下了一个看似耸人听闻实则十分正确的结论,即“爱就是谋杀”。而这不正是包丽所受到的伤害?就如包丽朋友在其文章中所说的,虽然法律上判定包丽是自杀,但当我们追溯所以然的时候,牟某的行为必然是需要纳入考虑的。
也正因此,齐泽克才会在纪录片《变态者电影指南》中指出,没有什么比被爱者更危险的位置了。他继承了魏宁格的观点,指出那些看似诉诸心灵的爱情最终却摧毁了真实的“被爱者-女人”的心灵存在。作为主动爱者的男性在主流性别意识形态中利用诸多污名和权力资源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或压制女性或摧毁她们。虽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包丽在这整段关系中的抗议、挣扎和反抗,但就最后的结果——包丽在自杀中写下“我命由天不由我”——我们发现个体的力量在此是弱小和有限的。作为“天”的牟某所代表的不仅仅只是他这一个个体,同时还有赋予他这一强势力量,甚至在背后支持他的整个性别体制以及各种性别污名意识形态。

齐泽克纪录片《变态者电影指南》剧照。
03 个体之间如何形成真实平等的连接?
在西方现代关于爱情和亲密关系的讨论中,许多人为爱情所赋予的力量其实也只是硬币的一面而已。传统异性恋之爱中内含强势的占有欲和唯一性,在某种程度上它既会是卢曼所谓的悖论式系统,但同时也可能造成欺压,因为爱情不是发生在一个“纯然之境”,它发生在福柯所研究和发现的各种权力-知识话语交错和再生产的现代社会中。由此导致在亲密关系中所出现的权力压迫就往往会变得一方面更加轻易和强烈,另一方面也大都难以察觉和很难进行判断。包丽事件之所以引起巨大关注是因为它的激烈程度,而更多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诸如冷暴力、精神控制和骚扰以及婚内性强奸等则常常被人们忽视。
当我们在一段亲密关系中向他人彻底敞开时,就往往会把自己置于十分脆弱的位置。在齐泽克分析卓别林的《城市之光》中,当曾经以为他是百万富翁的女孩看到自己一直喜欢的人是个流浪汉时,后者的处境是十分脆弱的。因为就如齐泽克所说的,一旦我们发现被爱者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怨恨和暴力就会产生。而在亲密关系中,无论是怨恨还是暴力能造成十分严重的伤害。

《城市之光》剧照。
在包丽和牟某的关系中,牟某通过各种信息对包丽进行的“创造”实则也反映了这个男人本身的诸多问题。在这里,有个细节我们也不能忽略,即牟某是包丽的学长,并且似乎在学校具有一定的名声,所以这也再次证明了在亲密关系中的权威所具有的“迷人魅力”和强权。而这也不正是层出不穷的校园男性教授性骚扰和侵犯女学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在牟某和包丽的称谓中,他要求包丽称其为“主人”,但他自己又称包丽为“妈妈”,这种看似矛盾的称谓其实也正反映了主奴意识在主体内部的同时存在。牟某看似强势的背后真正的原因是因其懦弱,例如他反复利用自杀来威胁包丽,正反映出其对“妈妈”的依赖;但他同时又对“妈妈”进行各种谩骂和骚扰,也反映出其某种根深蒂固的厌女/厌母情结。
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下,爱情是不可能的。在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的《他者的消失》中,作者指出,伴随着曾经作为令人不安的、焦虑的、地狱般的他者的消失,现代人开始了自我毁灭的过程,即“暴力辩证法无处不在:拒绝他者否定性的体系,会引发自我毁灭动向”(2019,页2)。伴随着“全然他者的否定性让位于同者的肯定性”,自恋便出现了——而“自恋者无视他者的存在。自恋者不断地揉搓、扭曲他者,直至在他者身上再度辨认出自己的模样”(2019,页32)。由此,“我”只沉溺于自我之中,从而出现了自我异化……牟某始终沉溺在自我想象中,因此他根本不可能真实地爱着包丽,把她作为一个平等的、值得尊敬的个体。
 《他者的消失》
《他者的消失》
作者: [德]韩炳哲 译者: 吴琼
版本: 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6月
造成这一局面的就如我们上面所说的,不仅仅只是牟某这一个体,赋予他力量且站在他背后的还有一层层的鬼魅:它们是韩炳哲所谓的现代消费和网络社会中的同一化深化所造成的他者的消失,进而产生了社会的自恋化倾向;同时还是传统看似消失实则变得更为隐秘、但却依旧强势的性别制度的迫害,以及关于女性气质的污名,关于性的陈词滥调,以及对于爱情神话的盲目塑造,对亲密关系中性别偏见与不平等的忽视……
在牟某和包丽的聊天记录中,我们发现前者一直滔滔不绝地说着,完全沉浸在自我的话语中,而彻底失去了倾听的能力。韩炳哲指出,“倾听并非被动的行动。它的突出之处在于一种独特的主动性。‘我’首先必须对他者表示欢迎,也就是说,肯定他者的‘他性’”(2019,页108)。肯定他者的“他者性”,也只有如此,个体之间才能形成真实且平等的连接。
如同阿兰·巴迪欧的《爱的多重奏》中所指出的,爱情具有的差异和同一的矛盾本身就是它的创造性源泉,是面向一种保存差异、接受他者的更理想的生活和生命体验,而非对于被爱者的消弭与吞噬;而在亲密关系中,对于性别制度意识形态这张“无声无息”的网的警惕、反思和批判,始终要求作为性别特权者的男性更为敏感与张开耳朵去倾听、去了解和具有同理心。
“我爱你”重要的不是“我”,而是我所爱的“你”。只有如此,或许才能打破“东风压倒西风”或“西方压倒东风”的暴力恶性循环。
作者:重木
编辑:董牧孜,走走;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