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李永博
当地时间8月18日,第77届世界科幻大会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公布了2019年雨果奖的获奖名单。今年的星云奖得主、美国作家玛丽·科瓦尔凭借The Calculating Stars斩获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电影《蜘蛛侠:平行宇宙》获最佳戏剧表现奖。
作为科幻文学界最重要的两个奖项之一,雨果奖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2015年,刘慈欣的《三体》英文版获得了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这是中国作家首次获得科幻文坛界的最高荣誉。一年之后,80后女作家郝景芳的《北京折叠》,又获得了第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在中国科幻赢得世界目光的同时,《流浪地球》等科幻题材的国产电影的上映,进一步掀起了科幻热潮,一些评论家甚至把2019年定义为“科幻元年”。
与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相比,科幻小说还是晚近出现的新生辈。直到 1840 年,“科学家”(scientist)一词才正式被人提出,而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的说法则要等到 1851 年才出现。优秀的科幻文学作品总是让读者去思考,是什么让当下与过往的时代变得不同,我们会走向一个怎样的未来,以及我们如何去应对变化中的挑战。
科幻文学那种“指向未来”的特征,不仅塑造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也对现实中的社会和公共政策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实际上,科幻文学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比我们想象得更为紧密。在历史上,科幻文学不仅推动了未来技术的发展,也影响了政治发展的格局。
航天机构为什么愿意同科幻作家合作?
在严谨的科学研究与流行的科幻小说之间,并非如很多人想象中那样泾渭分明。很多知名的科学家,十分热衷于科幻小说。
澳大利亚科学家Ian Chubb教授曾说,自己从《生活大爆炸》中学习到不少让科学变得有趣的方法。英国前科学部长Malcolm Wicks曾提议,教师在课堂上运用《星球大战》或《神秘博士》里的场景开启科学课的讨论。美国火山学家Jess Phoenix在竞选国会议员时,曾把一项环保行动与《星际迷航》中的宇宙观联系在一起。
除了科学家以外,一向追求“高精尖”的航天机构,也是不折不扣的“科幻迷”。刘慈欣就曾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的确有“国家级的航天机构与我联系”,他也提供了一些创意。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与科幻作品的合作,已有大半个世纪的历程。
1969年,在“阿波罗11号”登月的前夕,一部被后人奉为圭臬的科幻电影在好莱坞上映。《2001:太空漫游》能够成为经典,得益于NASA的大力支持。片中的飞船、空间站等元素的灵感均来自于NASA,导演库布里克更是花费了75万美元制作了一个高12米,宽2米,并真的能以5千米每小时的速度转动的太空舱模型。

电影《2001:太空漫游》剧照
近年来,好莱坞的科幻大作,从《世界末日》、《万有引力》、《火星救援》到《复仇者联盟》,背后无不有NASA作为金牌顾问。2014年,NASA还与出版社合作启动专项,帮助科幻作家们写出贴近科学原理的故事,不少美国科幻作家也是NASA的顾问。
在严谨求真的科学家与天马行空的科幻作家之间,为什么能够实现双向的合作?在刘慈欣看来,科学同样有赖于科幻中无惧无俗的想象力:“国内的专家会奇怪,觉得科幻作家懂什么。其实,我们的作用,就是启发航天工程师的想象”。
一部畅销的乌托邦小说,掀起了美国19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
科幻作品不仅受到科学界人士的青睐,历史上不少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也是忠实的科幻迷。从一国总统到渴求变革的普通人,科幻小说不仅为渴求变革的普通人浇灌了远大的理想,也为温斯顿·丘吉尔、罗纳德·里根、尤金·德布兹等政治领袖塑造了他们的行动方针与政治实践。
1888年,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位律师出版了长篇小说《回顾:公元2000-1887年》,该书出版后曾经风行一时,在美、英各地销售一百万册以上,作者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名字也因此蜚声世界。作者在书中畅想一位年轻的波士顿人陷入一个多世纪的沉睡,并在2000年醒来,同时发现美国已经成为了社会主义的乌托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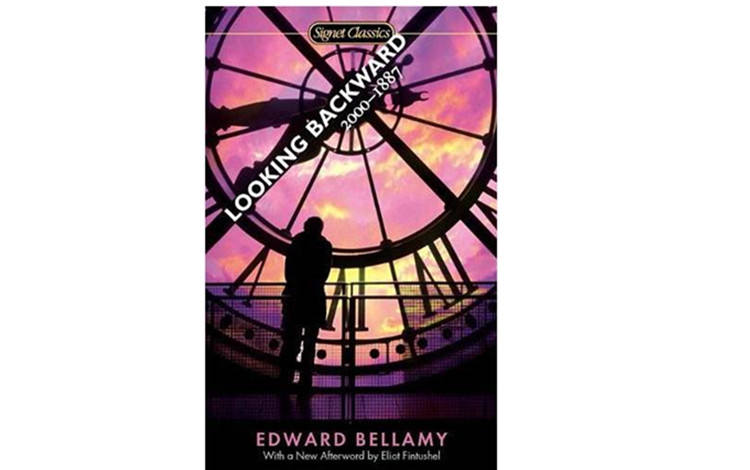
《回顾:公元2000-1887年》,爱德华·贝拉米著,Signet Classics 2009年版。
在一个没有资本主义的世界里,国家管理着一切,社会和技术进步高速发展,商品与服务的中间商被抹除了,普通人的工作时间减少了,大多数人都可以提前退休。贝拉米认为,摆脱了市场资本主义的美国人将会拥有一个更富裕也更有效率的理想社会。
《回顾》并不是第一本空想社会主义小说,但它恰好切中了时代症结,以至于推动了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社会主义运动的狂潮。那个年代的美国是贫富两端极为悬殊的国家,两次经济危机更是造成了数以万计的失业者。
当时社会主义在美国常被视为离经叛道的思想,《回顾》的问世让美国各地兴起“贝拉米俱乐部”,成员包括了后来一些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尤金·德布兹(Eugene Debs)、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和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据说英格兰的“田园城市运动”(Garden City Movement)也受到了这股思潮的影响。
丘吉尔的“科幻体”演讲话术
作为曾经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演讲才能与他的战时领导力一样出名。然而,他在演讲时的许多观点与话语,直接来自于英国科幻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
丘吉尔曾把纳粹德国的崛起称为“聚集的风暴”(the gathering storm),这一比喻就来源于威尔斯的小说《世界大战》(The War of the Worlds)。在阅读威尔斯的小说《现代乌托邦》(A Modern Utopia)后不久,丘吉尔就在格拉斯哥的苏格兰自由委员会面前发表讲话,主张进行社会改革,而演讲内容则呼应了威尔斯的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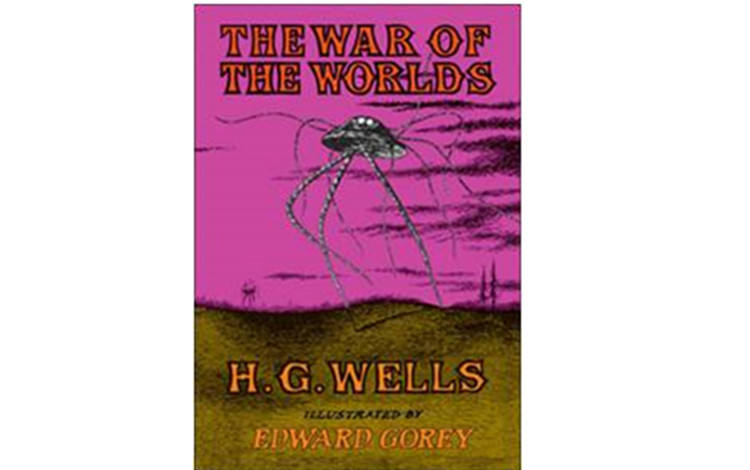
《世界大战》,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著
就在演讲前几天,丘吉尔还写信给威尔斯说,“我欠你一大笔人情。”威尔斯对丘吉尔的影响不仅仅涉及话语与社会理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斯就建议丘吉尔建造一种堑壕战装置,尽管后来由于进展缓慢而无法被使用。直到威尔斯1946年去世,丘吉尔与这位小说家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
美国自由党、激进的个人主义哲学与“反文化”运动
科幻小说中的乌托邦理想给予人的力量之大,甚至能够孕育出政治党派。1957年,俄裔美国作家、哲学家安·兰德的乌托邦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在美国出版,尽管恶评如潮但畅销无比,一时之间对美国大众的影响仅次于《圣经》。安·兰德在小说中推崇的极小化政府的个人主义,深深吸引了一位名叫大卫·诺兰的年轻人,后者在1971年根据小说的精神创建了美国自由党(Libertarian Party)。美国自由党至今仍援引安·兰德的作品来彰显其价值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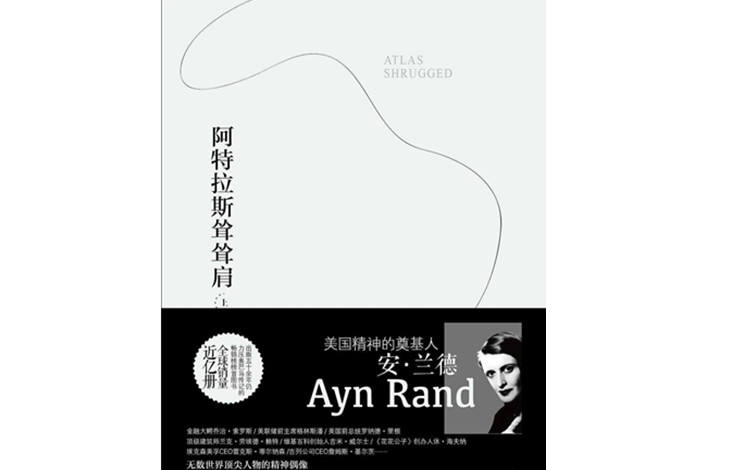
《阿特拉斯耸耸肩》,安·兰德 著,杨格 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
在个体被无限张扬的年代里,另一位让无数年轻人为之倾倒的精神偶像是罗伯特·海因莱因。如今被誉为“美国现代科幻小说之父”的海因莱因,不仅创作了大量经典科幻作品,也曾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文化热潮的先锋。
在那个年代里,美国军事学院与嬉皮士社区的教室到处可见海因莱因的小说《异乡异客》。书中描绘了一位来自火星的神秘人士,他的精神信念与嬉皮士们所信奉的“爱、永恒与纯真的理想”不谋而合。在崇尚偶像破坏和自由性爱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海因莱因的科幻小说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文化象征。
里根的“星球大战”:科幻作家组成的决策团队
在政治谋划与科幻想象的互动中,最为疯狂的一次实验,莫过于罗纳德·里根主导的“星球大战”计划。里根一直痴迷于科幻小说,从小就阅读美国科幻作家埃德加·巴勒斯创作的《人猿泰山》、《火星》等史诗般的冒险故事。在里根看来,科幻小说不仅仅是毫无根据的幻想,他相信科幻小说作家能够对技术和未来的发展提供宝贵的意见。

美国总统里根在阅读文件。里根与撒切尔夫人、约翰·保罗二世三人被合称为“驯熊三人组”,他以“星球大战”计划和一系列战略“组合拳”给苏联以沉重打击。
1983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在直播采访中向电视机前的美国民众宣布,美国将在未来几十年里投资上万亿美元,研发足以抵御洲际弹道导弹的战略防御系统。据说这个系统将装备一系列太空X射线激光器,可以探测并转移任何朝美国发射的核武器。
这一近乎科幻的设想与天文数字般的资金投入,让不少政治家和科学家感到不切实际,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将其称为“不计后果的‘星球大战’计划”,这一名字也由此被流传下来。
如果看一看当时美国航天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构成,也许就更能理解参议员肯尼迪的担忧了。除了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外,里根总统麾下的顾问委员会包括了一大批当时著名的科幻小说家:波尔·安德森(Poul Anderson)、格雷格·贝尔(Greg Bear)、罗伯特·海因莱因、吉姆·班恩(Jim Baen),以及委员会的召集人、科幻作家杰瑞·波奈尔(Jerry Pournelle)。
这些科幻作家最初的职责是帮助里根团队完成过渡,以适应其在太空政策中的新角色,但最终成为了政府决策班子的一部分,为里根团队起草了几份太空政策文件,包括说服里根推动“星球大战”计划。
冷战背景下产生的星球大战计划,最终注定成为了一个费力不讨好的狂想,一场漫长、昂贵而无用的冒险。然而,科幻作家与国家航天局的合作,却从此成为了不少国家发展航天技术的传统。
科幻文学的审议精神:公共决策的试验田?
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科幻小说的价值萦绕于自由畅想的精神世界。在科幻作家与科学界、政治界合作越来越紧密的今天,科幻作品究竟能给现实世界带来什么?
毫无疑问的是,不少科幻经典的幻想,如今已经成为了现实。艾萨克·阿西莫夫在1952年发表“银河帝国三部曲”的时候,书中描绘的扫描仪、复印机、笔记本电脑、指纹扫描,如今都已成为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科幻作品的问题指向,往往也并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过时。1818年玛丽·雪莱创作的《弗兰克斯坦》,被称为第一步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当时很多人仍然把科学这种新兴事物视为异端。人类命运与科学进步之间的冲突,能够得到解决吗?200年后,《弗兰克斯坦》抛出的母题仍然没有过时,克隆技术、基因编辑和人工智能技术遭遇的伦理困境,就是这个时代的“弗兰克斯坦”问题。

电影《科学怪人》(1931)剧照。
澳大利亚首席科学家Alan Finkel,曾在2017年做过一次主题演讲,向台下的政商精英和领袖讲述“为什么政商领袖需要多读一点科幻文学?” Finkel认为,科幻文学不仅为技术的发展提供想象力,也可以作为公共决策的一种补充审议形式。
当代技术发展的速度,往往让立法和公共政策难以跟上时代变化的脚步。从云端大数据处理、虚拟现实技术到移动支付、共享单车……新兴事物层出不穷,由此产生的社会与法律问题让各国的立法者头疼不已,公共审议和论证也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然而,这些现实生活可能遇到的新问题,在科幻小说中早就出现了。远远早于问题实际发生之前,科幻作家们已经在思考未来世界可能遇到的困境,譬如信息时代的个人隐私、克隆婴儿的伦理问题等如今困扰我们的问题。科幻小说通过具有想象力的文字来“模拟”未来世界的可能性。
作家们给出的处方未必就一定是正确的,科幻作品也不可能成为技术与立法的指南。一些科幻作品,或陷于乌托邦的白日梦,或陷于反乌托邦叙事的厌世与悲观,或是片面地崇古贬今,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假想的古代。然而,这不妨碍科幻文学能够为公共决策提供自由讨论和试错的空间,成为未来技术与公共决策的试验田。
参考资料:
https://asiancorrespondent.com/2019/08/sci-fi-as-a-potent-political-tool-how-popular-fiction-shapes-policy-debates/
https://australiascience.tv/alan-finkels-science-fiction-for-leaders/
https://thestateofsie.com/the-day-after-tomorrow-climate-change-anthony-leiserowitz-global-issues-audience-behaviour/
作者:李永博
编辑:李阳
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