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引起巨大关注的电影《流浪地球》中,设置了一个气候发生巨大改变之后已经濒临崩坏的极端严酷的气候环境。在很多地区频繁出现的恶劣天气中,这样的末日景象,也许不仅仅是一种想象。近日,美国中西部地区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极寒天气,明尼苏达州、威斯康星州和伊利诺伊州最低温度都降到了零下52摄氏度左右。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正经历最低达零下50度的极寒,场面堪比灾难大片。
美国极寒、欧洲高温、特大洪水……这些年的极端天气事件频频袭击世界各地,很少有地区能够幸免。如果关注西方主流媒体,我们会发现气候变迁的议题隔几天就会占据重要版面,气候变迁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日常。
面对气候变迁这一关乎全人类的议题,著名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悲哀地发现这样一个简单事实:气候变迁在当代小说中的存在感远远低于它在公共讨论中的存在感。在文学里,当气候变迁出现时,几乎永远与非虚构联系在一起,而以虚构为己任的小说则对之视若无睹。以至于高希开玩笑地说,提到气候变迁这一议题往往足以把一个小说“降格”到科幻小说这一类型文学的范畴。

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1956年7月11日生于加尔各答,成长于印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等地。他曾是田野工作者,也曾任职记者,但最终他成为一个小说家。代表作品包括《理性环》《加尔各答染色体》《玻璃宫殿》《罂粟海》《烟河》等。《罂粟海》入围2008年英国曼布克奖决选名单,2007年高希被印度总统授予印度最高荣誉“卓越贡献奖”(Padma Shri)。
高希以“鸦片战争三部曲”《罂粟海》《烟河》《烈火洪流》赢得世界声誉,2016年,他出版了学术随笔《大紊乱:气候变迁与不可思议》(The Great Derangement: Climate Change and the Unthinkable)一书,从文学、经济和政治的角度分析当代世界对气候变迁的认知。在第一部分关于文学的篇章里,高希提出了一个问题:小说里的气候变迁去哪里了?或者说,小说如何书写气候变迁?
高希发现,就英语文学而言,只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伊恩·麦克尤恩、冯内古特、多丽丝·莱辛等少数几位作家处理过这一议题。而尴尬的是,高希自己尽管长期关注气候变迁,但他的小说里也几乎没有怎么处理过这个问题。
在高希看来,不仅小说这一艺术形式对气候变迁失语了,更广义来说,整个当代文化都很难对气候变迁做出很好的处理,他认为气候危机也是文化的危机、想象力的危机。高希认为,文化生产欲望,比如汽车生产的是自由、速度的现代想象。他自问,作为一个小说家,当他在描写人物时,选择用名牌作为元素时,是否该问自己,在何种程度上这让他变成了市场操控的同谋者?他也质疑,如果建筑师们偏爱建造玻璃金属材质的楼塔,是否要问,背后生产了什么样的欲望?

电影《后天》剧照。
而回到小说,高希提出的问题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就其形式而言,与气候变迁这一主题之间是有张力的。初看之下,这似乎很难理解,为什么小说里要书写极端天气会对小说家来说变成一件难事。高希自己遭遇过特大飓风,但他多次努力,都没法让自己的人物走在路上被飓风击中。一个解释关乎可信度。如果在小说里,一个人物突然遭遇罕见的天气事件,这会被视为作家想象力枯竭的表现。而现代小说的一大特征就是,把那些闻所未闻的事物搁置于背景,而让更日常化的事件置于前台,只有科幻小说这样的类型文学或带有幻想意味的小说会去处理那些概率极低的事件。对于小说家来说,即便是那些在现实生活中稍微不同寻常的、不太可能的事情,如果写进小说,也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让读者信服。因此,也不难想象,一个人物好端端走在路上,突然被飓风击中这样的场景,对于作家来说,要营造这样的情节有多难。
而气候变迁所带来的极端天气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极度不可能性,也正因此它与现代小说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张力,于是会出现现实主义流派的小说对气候变迁这一重大现实视若无睹这样颇有讽刺意味的现象。
在风起云涌的20世纪现代文学史上,也有如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这样的文学运动会处理那些看似极度不可能的事件,然而,问题恰恰在于,我们所面对的气候变迁完全是真实的,极端天气事件并不发生在《后天》里,而是真真切切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果以魔幻或隐喻的方式来处理它们,则会面临伦理上的诘问。
日前,新京报记者就气候变迁与文学这一问题对高希做了专访。
小说家还没找到介入气候变迁问题的方式
新京报:在书里,你提出诗歌和气候变迁这个题材之间有更亲密的关系,这怎么理解?
高希:事实上,我想说的是,散文和小说(就定义来说,这两种文体)都得符合一种期待,就是得读起来像是可信的,写的事情是可能发生的,但诗歌不需要符合这样的期待,你写的东西真不真、可信度有多少对于诗歌来说无所谓。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通过诗歌来处理那些气候变迁中典型的“非常不可能的事件”是更容易的。
新京报:有一种观点认为,小说家为什么很难去书写气候变迁是因为很难与遥远的气候事件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对你来说这会是一个问题吗?
高希:我不认为极端的气候事件距离我们的远近和小说家无力书写它们有什么必然的关系。我们这个时代的气候事件已经不再“遥远”。你就想想加利福尼亚的野火吧或让纽约和休斯敦遭受重创的飓风。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处地方距离这些极端天气事件是遥远的。

《追日》,作者: [英]伊恩·麦克尤恩,译者: 黄昱宁,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6月
但同时,气候变迁这个议题体量之庞大确实给小说家造成了巨大的书写困难。在这样的语境下来阅读伊恩·麦克尤恩2010年出版的《追日》这部小说就很有意思了,事实上正是因为这个主题的庞大最终把这个小说推向了讽刺。你会发现麦克尤恩是关心气候变迁的,然而小说这一特定的形式让这本书推向了某个特定的方向。《日出》变成了一个讽刺小说。你可能称之为“资产阶级的复仇”:以某个角度或甚至深入思考气候变迁都变成了一个荒诞的事情。
新京报:气候变迁挑战了我们对于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等概念的认知,就像你在书中说的,往往是科幻小说或非虚构文学在处理气候变迁这个议题,而在所谓的严肃小说那里的呈现极其匮乏,你能否再谈谈这一点?
高希:我们正处于一个新时代的边缘,在这个新时代里,我们过去的那些思维和行为习惯都像眼罩一样妨碍我们去感知我们当下的现实处境。世界各地的作家、艺术家和思想家都在艰难地寻找到有效的概念和理念,可以让我们介入这个新时代里这些前所未有的事件。但发现这些介入的模式是需要时间的,而我们当前确实没有找到。
新京报:在一个访谈里,你提到,那些被视为严肃小说的作品其实就是退回到了闺房、个人内心的那种作品。这里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你说的资产阶级心态(bourgeoismentality)或资产阶级美学有关。这也跟你提出的质疑有关,为什么中产阶级和富人们这么偏爱住在靠近水边、海边的地方。但实际上当遇上超大台风这样的极端天气,这些人恰恰最容易受打击。因此,你觉得如果要解决气候变迁的议题,我们有必要摆脱这种资产阶级心态吗?
高希:资产阶级文化的普遍趋势就是朝向一种必胜的信念(triumphalism),就是征服外部世界。当然,这类态度是和种族、殖民主义这样的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然也被视为一个需要被征服、主宰和利用的领域。这种观念的盛行显然会给我们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以后变迁构成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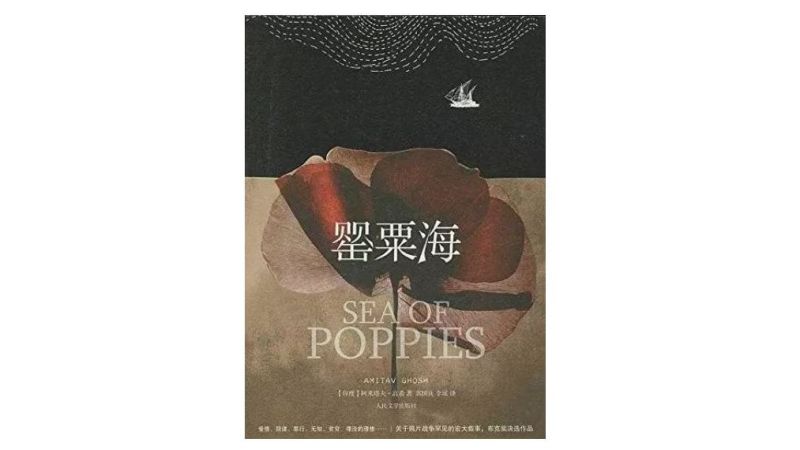
《罂粟海》,作者: [印度] 阿米塔夫·高希,译者: 郭国良 / 李瑶,版本: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10月
新京报:书里有一个地方给我印象深刻,你把对于气候变迁的分析引向了一个更大的议题,就是气候变迁挑战了现有的关于人类和非人类能动性的认识论框架的,以及那些非人世界(如过去社会里那个有泛灵论的世界)的能动性则构成了我们在书写气候变迁这一议题时想象力的失败。
高希:在整个20世纪,所有的艺术都越来越以人类的心灵和感受为中心,也越来越与物质世界脱节。如果你去想一下上个世纪所有重大的文学和艺术运动,你就会发现都有一个越来越抽象化的趋势。与之进行对抗的一些运动像“社会现实主义”等则无一不被边缘化。当然,这里有重大的政治因素,比如冷战的意识形态。但无论如何,造成的效果就是我们失去了那种和周遭世界联系的感觉。在这个意义上,以人类为中心似乎基本上是“现代性”的后果。用另外的话说,把温室气体排入大气层似乎也是掩耳盗铃,我们越来越紧密地关注在人类身上反而让我们无视气候变迁的恶果。
新京报:书里有一个观点很有启发,你说那些与先锋为伍的所谓的现代小说淡化情节,但实际上如果从气候变迁这一个视角来看的话,这类小说其实是落后的,你的意思是现代小说走得太远了吗?
高希:20世纪的现代主义的一大显著特征就是先锋(avant-garde)的理念——艺术家和作家走在文化和历史的前沿。当然,就像我在书里写到的,艺术家和作家确实引领了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运动。然而我也认为,很显然,在气候变迁这样的问题上,艺术家和作家没有做出很好的回应。这确实让人费解,而《大紊乱》这本书就是试图处理这个问题。
受气候变迁、极端天气影响最重的,
不是穷人,反而是中产阶层
新京报:你在书里强调,在气候变迁这个议题上,亚洲应处于讨论的中心位置,你还进一步谈到现有的关于全球变暖的话语基本上是欧洲中心的,为什么亚洲的中心性没有得到广泛承认?
高希:关于气候变迁的话语和叙事依然是高度欧洲中心主义的,但我们亚洲人也难辞其咎,因为我们没有足够关注这个议题。
新京报:你强烈反对碳经济,而且通过引述甘地的思想,你似乎认为亚洲应该停止拥抱那种发展主义的路线。但你这样的观点在印度或中国可能会受到批评。有人会说:“无论如何,我们首先得致富啊”,你会怎么回应这样的看法?
高希:我想我们得重新思考“富裕”的意义。如果你呼吸不到干净的空气,喝不到干净的水,或因为担心极端天气事件降临而无法安然入眠,那你就不是富裕的。事实上,你的生活质量是很糟糕的。
新京报:你在书里说穷人可能抗压性更强,面对灾难更有弹性,这是不是气候变暖这样的问题在印度不被视为什么大问题的主要原因?
高希:在印度,有很多人会说“哦,受害的会是穷人”,但也很可能,那些受气候变迁、极端天气影响最重的反而是中产阶层。你看看近些年孟买和金奈的极端暴雨。在印度,城市贫民通常流动性很大,他们在乡下有联系,经常在城市和乡村间往返,他们也知道怎样更好地利用火车。他们可以提前一个月就移动。在孟买这样的城市,一旦发生大风暴,城市贫民就可以很快转移,但资产阶层就不行了。问题不仅仅在于他们能不能转移,而是说他们压根儿就不想离开。对很多中产阶层来说,他们的房子或公寓就是他们最大的财产。他们没法丢下一走了之。他们整个人生都是建立在某种稳定性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是所谓的资产阶级生活。但如今这种稳定性在任何地方都难以为继了。现代国家所提供的基本保证——如稳定、安全——都烟消云散了。
身份政治遮蔽了气候变迁,
这是关乎人类集体生存的大问题
新京报:你在书中写到气候变迁这个事情没有在印度引发多大的热情和关注,事实上,人们的政治能量越来越聚焦在那些与身份有关的问题上:宗教、种姓、性别权利等。我觉得中国也一样,但是是以另一种方式。比如,在中国,人们会担忧雾霾,但笑一笑也就过去了,也就适应了,这其实也是无为。
高希:我不太清楚中国是什么情况,但是在印度,事实是,气候变迁几乎从来不在政治讨论的范围之内。在印度,你翻开报纸或打开电视就会发现,有很多议题比干旱或农业危机这样的议题得到的关注多得多。在印度的政治阶层中间,这种对于气候变迁的漠视太可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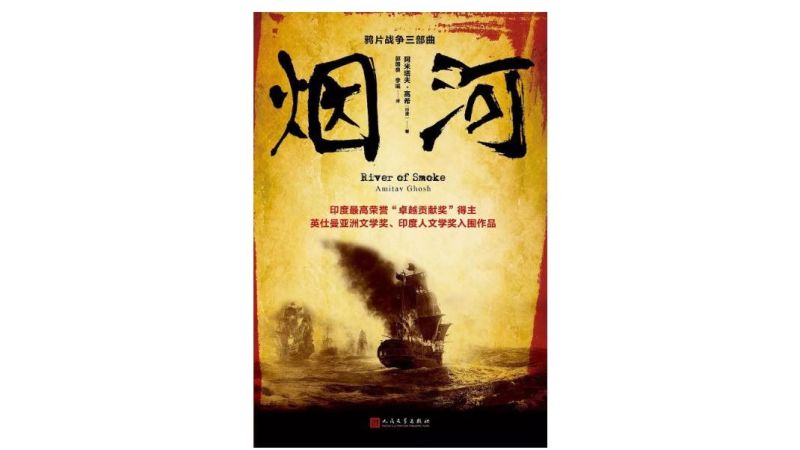
《烟河》,作者: [印度]阿米塔夫·高希,译者: 郭国良 / 李瑶,版本: 99读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8月
新京报:说到身份政治,你认为如果要点燃人们对于气候变迁这一话题的热情,身份政治是有效的吗?
高希:不管你看印度还是美国,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今天政治的话语就是身份政治。实际上这和政治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考虑的是,首先,所谓的“政治”应该关乎生存、集体福祉等等。但我们今天看待政治,或政治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基本上是身份认同的议题。这些身份政治的议题完全遮蔽了全球气候变暖这种关乎人类集体生存的大问题。
新京报:在书中,你认为你不太认同那种把资本主义看成气候变迁的始作俑者的观点,你认为看待帝国是看待这一问题的另一重棱镜。“即便资本主义明天会发生神奇的改变,那种想要追求政治和军事上的主导权的冲动依然会对减缓气候变暖的行动构成障碍”,能否再谈谈这一点?
高希:气候变迁经常被视为一个经济问题,是由消费、生产、分配以及这些过程中产生的排放所引起的,用别的话来说,这就是“资本主义”的题中之义。这种思维框架的主导也许是经济主义的思维模式深入渗透到了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造成的后果。但在我看来,这种经济主义的归因框架往往会掩盖其他同等重要的方面,比如国家间的军事竞争、主导和被主导的关系,或更宽泛地讲,也就是“帝国”(Empire)的动力。这种掩盖以不同的方式发生在不同的层面。比如,像纳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等很多人都持资本主义是主要的气候变迁的动力这一观点,仔细想想的话,就会发现,问题是资本主义不是同一个东西:我们现在知道东亚资本主义是劳动力密集型的,而不是资源密集型的,就生态足迹(ecologicalfootprint,指的是一种测试人类对资源生态消费的需求与自然所能提供的生态供给之间差距的方法)来说,东亚资本主义要远远小于英国和美国所流行的那个版本的资本主义。然而,英美模式的资本主义最终变成了世界主导,如果你不把帝国主义、全球争夺的历史纳入视野的话,你就没法理解这一点。
作者:沈河西
编辑:徐悦东 校对:薛京宁
原标题:《流浪地球》里的极端气候,为何很少出现在当代文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