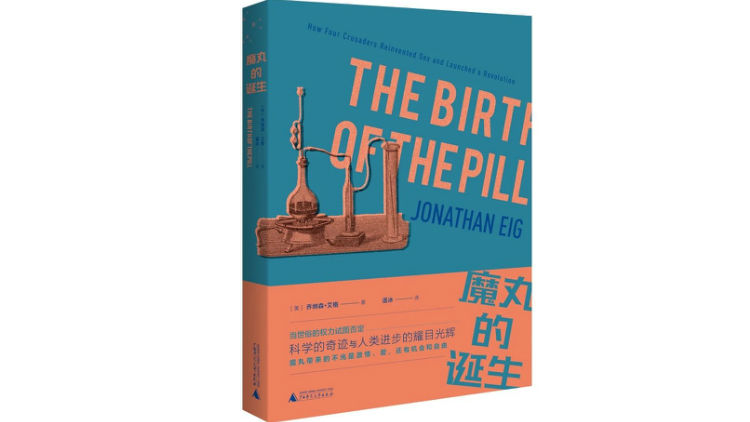
《魔丸的诞生》,作者:乔纳森·艾格,译者:语冰,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1月。
拉个草台班子,打场不可能成功的仗
二战后,美国曾经进入了生育高峰引发婴儿潮,1960年,美国女人平均每人育有3.6个孩子。人口爆炸给社会和政府带来极大的压力,降低人口势在必行。但是女性们发现,尽管她们已经感到抚育压力,不想再生产,可是掌握生育的决定权却不在她们的手上。当时流行的避孕措施是使用避孕套,但是那会儿性是件羞于开口的事,而要得到它们需要拿到医生处方。
更令女性担忧的是,是否使用避孕套的决定权,更多掌握在男性手上。考虑到使用感、获取途径或生育目的,即使有避孕套,女性往往也没有办法阻止性行为带来的不断怀孕的结果。而避孕药的诞生给女性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权——不必纠结男性愿不愿意使用,女性自己掌握主动权。而这也促进了它发明的初衷,让女性更好地享受性爱。
20世纪传奇式的社会改革家玛格丽特·桑格很早就开始普及“节制生育”的理念。她发现如果女性在性关系中的地位没有提高,那么她们就永远无法真正获得平等权益。桑格71岁的时候还在期待能够找到一种顺应生理需要,让女人能够每天早上用橙汁送服的药。这种药既能够让她们享受性又不会影响生育,还可以在全世界推广。在许多科学家那遇冷之后,桑格终于找到一位愿意和她一起通过科技解决法律完成不了的事情的人,这个人就是被称为“弗兰肯斯坦”的科学家格雷戈里·平克斯。
于是,创造避孕药的历史就从这个草台班子开始了。

1967年《时代》周刊封面,将避孕药摆成女性的符号。
1967年,《时代》将避孕丸放在杂志封面,并且报道称在其问世的短短六年内改变了美国人的性生活和家庭生活,未来它将改变全世界。但是这个改变全世界的药丸的诞生之途并没有那么顺畅,或者说随便一个差错我们都可能见不到它。
 玛格丽特·桑格。
玛格丽特·桑格。
用现在的话来说,桑格的一生就是“战斗的一生”。她从年轻时就是女性主义者和性自由主义者,因为受到《反淫秽法》的四项罪名指控,她离开丈夫和孩子搬到了欧洲。她有自己的坚持和理想,这个信念也一直支撑她不断离开家庭投身于自己的事业中,选择和当时美国近八成女性不同的人生道路。尽管已经七十几高龄,但是让女性享受性的心愿几乎成为她给自己人生定下的最后一站目的地。

格雷戈里·平克斯。
而这时,天才式科学家平克斯因为自身的狂傲和一些人的反犹情绪被赶出哈佛。在前同事的帮助下他终于勉强在克拉克大学找到一份工作,并且可以继续在实验室里用兔子研究超前的试管培育方法。虽然事业遭遇滑铁卢,但是平克斯天生就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型科学家,相反,他既能够预见科学趋势并且以极大的热情扎进实验里,同时他也明白让科学成果被世俗接受同样重要。

约翰·洛克。
当他接受桑格的提议开始研究避孕药的时候,他就明白将来总有一天他要面临公众、法律、教会的三重抗议——公众将质疑避孕药助长滥交、法律需要平衡世俗和价值观,而教会本身就反对堕胎。所以,尽管避孕丸还没有发明出来,但是它需要一位推广大使,他想到了约翰·洛克。洛克出身工人阶级家庭,奋斗进入哈佛,是科学家、医生,同时也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总是穿着精心定制的西装、时刻打领带,但是并未摒弃自己工人阶级的根,所以既不招摇又绅士的言行举止让他成为了一名好莱坞明星式的医生。当然仅仅是这样并不能打动平克斯,最重要的是洛克关心病人。天主教禁止堕胎,但是洛克认为如果危害到母亲的健康那就应该立即终止妊娠,为此他公开反对自己的教会,被开除教籍也在所不惜。有了洛克,后期说服公众参与试验和接受这种药丸就变得容易一些。

凯瑟琳·德克斯特·麦考米克。
科研需要大量的经费,桑格虽然提出想法,但是她却没办法搞来资金,更别说现在拿着微薄薪水的平克斯了。但是巧合的是在桑格和平克斯会面前不久,凯瑟琳·德克斯特·麦考米克寄了一封信给桑格。这位女士是当时全世界最富有的女人之一。她个人生活极为不幸,作为麻省理工首位女毕业生,她在婚后才发现丈夫患有精神分裂。由于医生不让丈夫与她相处,她将全部的热情投入到女权运动之中,丈夫去世之后她继承了全部遗产。她迫切希望这种避孕丸快点研究成功,于是她以出资人的身份,不停地催促平克斯和洛克,并且让桑格利用她的社会声望大力宣传。
就这样,是命运也是人为,一个仓促组建但是分工合理的团队开始创造这种“魔丸”。
事实上,还有更多的巧合。比如,平克斯公开研究避孕丸的克拉克大学就是1909年弗洛伊德(主张性与个人自我的心理学)和荣格开办讲座的地方,这里有着更为开放的风气;比如,当时欧洲流行的避孕丸沙利度胺致畸惨剧还没有在临床实验中发现;又比如,关于性自由的讨论已经开始在美国社会里蔓延开来。
在性和婚姻的牢笼里,杀出一条路
除了会使用火,人与动物还有一点区别,那就是多数哺乳动物的性行为仅仅是为了繁衍后代。
科学家研究动物这一行为时发现,在大多数动物看来不以繁衍为目的的交配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甚至是危险的,因为容易大意而被天敌乘机偷袭。

雌性狒狒、长臂猿、猕猴都是进入排卵期才开始交配。图片:视觉中国
可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就曾犯过动物式的困惑。
性行为的目的只能是为了繁衍,如果有别的念头或行为即为罪孽。罗马天主教的教义如是说。
全世界的文明都不约而同地遵循这一教条:《旧约》里,当莎拉不能为亚伯拉罕生育子女时,亚伯拉罕纳侍女为情妇;中国古代女子七出之一,无子,去;所罗门王不仅有几百个妻子,还有成群的妾;而在罗马帝国,犯下通奸罪的女人会被逐出家门,禁止再嫁。
性是繁殖的性。被认为是繁殖主体的男性可以享受齐人之乐,作为繁殖载体的女性如果无法履行这一目的,就失去自身的价值。
所幸,人类关于“性的意义是什么”的困惑慢慢得到解答了。得益于文明的不断发展,人们从道德到世俗层面都摒弃了以繁衍为目的的性,我们明白人的性是出于爱的行为,因此一夫一妻制不仅在法律上规定下来,也逐渐成为世俗的共识。
可是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一开篇就讲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类的婚姻制度虽建立在情感与性爱的基础之上,其目的却不在于完成情感与性爱,而是为了确保有一个稳定的、抚育后代的社会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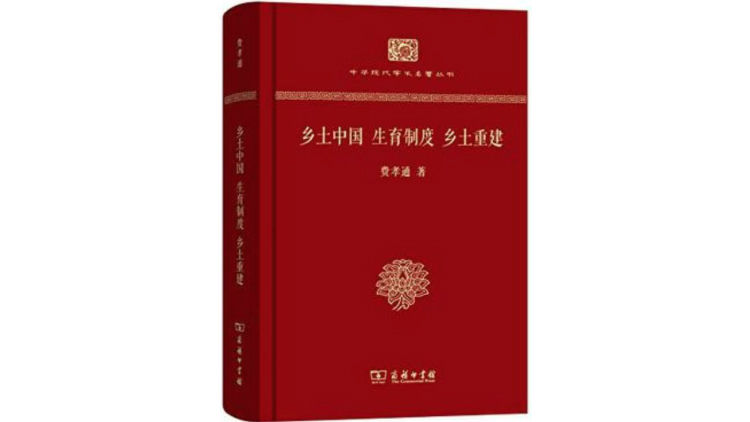
《生育制度 》,作者: 费孝通,版本: 商务印书馆 2015年8月。
性是女性为了抚养后代,与其伴侣的交换行为。这是人类学家长期以来所鼓吹的一套理论。女性,尤其是远古时期,由于无法独自抚养后代,她们必须通过不断满足伴侣的需求,从而保证获得抚养后代的助力。这个说法虽然不是人人都认可,但是它某种程度上应和了婚姻形成机制——基于男女双方协作的抚养体系。
但是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在桑格和平克斯正在计划制造一种便宜、易操作、万无一失的避孕药丸的时候,建立在情感、性爱、繁衍等基础之上的婚姻以及家庭关系里,这种抚育机制存在致命的缺陷。
统计数据显示,在波多黎各,55岁以内的妇女平均育有6.8个孩子。而在美国,战后的婴儿潮导致每个家庭普遍拥有3-4个孩子。可是承担抚育孩子的责任并没有像制度规划的那样由男女均摊,相反,这就是女性一方的责任。以致于当女性得知平克斯的研究之后,来信寻求帮助:
一位来自加拿大的30岁妇女写道:“我真的需要您的帮助,我想我不适合抚养十个或者更多的孩子。成本太高了,而我的丈夫也没有在教育我的(在此处她划掉了‘我们的’)孩子方面给我什么帮助......请帮助我。”
除了不停地受孕、生孩子或者是冒着生命危险堕胎之外,对于女性而言,不断增长的家庭人口使得她们再次被牢牢地束缚在家里。1970年,有婴儿的妇女中有80%留在家里照顾孩子。
性自由、婚姻、家庭概念、女性权益这些概念杂糅在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社会改革运动中,让许多人意识到这种神奇的药丸或许能够带来突破。
被误解的性自由和避孕药
桑格一开始制造避孕丸的目的非常直接,希望女性能够享受性爱。没有负担,没有顾忌,顺应生理和心理的需求。但是包括她自己和团队的其他人都明白,这样的理由看似非常合理但是不具有正当性。教会和公众担心这样会导致家庭关系瓦解,并且是变相在鼓励性滥交。
但是,在这些避孕药倡导者的观念里,性是人性,性自由是基本的自由,倡导这种自由并不等于倡导滥交。将这两种不同的状态等同无疑是对人性的压制。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学,将性和饥饿和渴的需求认为是本能需求,认为本能需求的发展影响着个体自我认知的形成。事实上,阿尔弗莱德·查尔斯·金赛通过调研发现大家对性的渴求远比公众认为或者表现的更为强烈,但是大家似乎已经习惯对这个话题避而不谈或是选择性忽视。对性与自我情感之间关系的探究和表现在艺术家这里尤为明显。

20世纪70年代,布鲁克林街头。
20世纪60-70年代是避孕药诞生的年代,同时也是性解放的年代。以纽约城为中心色情业在此蓬勃发展,曼哈顿还因此被称作风月之城。可是从事这项眉来眼去事业的人,有多少是被这场所谓的“衰退”浪潮所裹挟的。美国著名艺术家大卫·沃纳洛维奇就是其中之一,作为被父母踢来抛去行为的受害者,他被迫和其他人一样过早地迫降到危险的街头世界。生存意味着交易,最简单赤裸的交易。这段经历在他后来的人生里变成无法摆脱的包袱,也成为他用艺术形式试图去愤怒反抗的对象。童年就开始累积,到了成年之后挥之不去的异于常人的标签,让他格外孤独,性反而成为他不时与人亲密的方式。他说这是让他“从内心生活的静谧中释放出来”的渠道,最终变成别人愿意去倾听你的方式。

大卫·沃纳洛维奇。
这或许为我们理解性与自我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即性是一种关系,是无法言说之人自我表达的方式。不过这个视角在当时推广避孕丸的过程中并不能被人们很好地理解。
所以平克斯他们找到了一种折中策略:打着为了身体健康和控制人口过度增长的旗号,既能够在药品监管申请上又能在政府和公众那里有个交代。不过在那些有节育需求的女性那里,她们都明白事实是怎么一回事。从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美国的人口控制就变成社会改革女权派和政府之间的共谋和共赢。遗憾的是,这种药品没有在大洋对岸的亚洲国家流传开来。
中国古代很早就已经有关于避子药的记载,《山海经》中提到一种叫“蓇蓉”的植物,可以“食之使人无子”。之后不管是在唐代的《外台秘要方》还是孙思邈的《千金要方》里都有关于避孕药物的记载。避孕药物五花八门到包括植物,如藏红花、角刺茶;动物,如蝌蚪、水蛭;熏香,如麝香、熏草;还有针灸按摩等。但是很多汤药的原理其实是通过轻微毒性避子,含有水银、汞等,更多是堕胎之用,长期使用就有绝育的风险。
或许正是这种药长期以来给人留下可怕副作用的印象,即使到今天很多人对避孕药的疗效和功用还存在误解。而大众所熟悉的避孕方法除了避孕套就是结扎和上环。但是,不管是现实所见还是新闻报道,女性意外怀孕所要承担的风险其实是更高的。而早在五十多年前就已经诞生的药物,不仅没有成为掌握在女性手中的自我保护的工具,相反,最后让女性采取更为残忍的方式伤人伤己。这种倒退的代价不管对女性还是社会来说都是沉重的。
讽刺的是,那些随处可见的“不孕不育”或者“无痛人流”广告仍然将女性的身体当作是工具,相反关于避孕药的普及显得格外匮乏。如果回归避孕药的发明初衷,它就是为了鼓励女性享受性。而能够享受性这件事对于女性意味着重构自我身体的功能,摆脱注定生育的命运,可以获得与男性一样自由支配身体的权利。同时获得开发自我身体,发现乐趣的钥匙。因为如果女性羞于正视自己的身体,漠视最本能的渴望,那么无论何时我们都会被这种来自生理上的“自卑感”包裹着。不论外表与年龄如何,西方女性似乎对性更加自在。这是个无伤大雅的调侃,但它所表明的中外女性不同的性观念、身体观念仍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我们。
作者:朱雅云
编辑:走走 西西
校对:薛京宁
原标题:避孕药的诞生:它如何悄然改变了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