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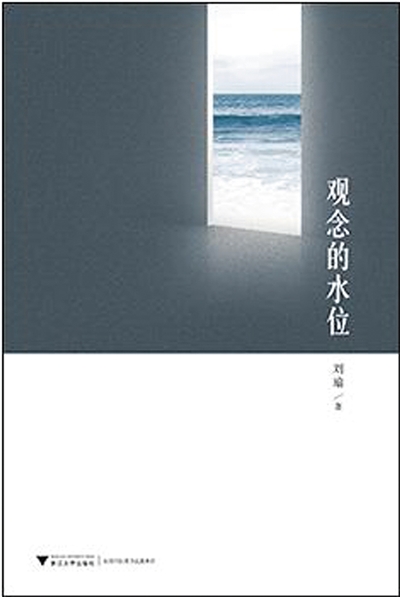
《观念的水位》 刘瑜 著
浙大出版社 2013年1月

《送你一颗子弹》,政治思考随笔集,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1月

《民主的细节》,政治思考随笔集,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6月

《余欢》,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

《那么,爱呢》,小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11月
她可以算智识活动上的劳模。这起自她澎湃的好奇心。当很多人习惯于在思维上“偷工减料”,“多快好省”地得出“豆腐渣”结论时,她却有“丁是丁,卯是卯”的安全施工的自觉。
她很少让文章穿着登高鞋或者装扮成圣诞树出来,在她看来,一个道理的意义不在于它能创造多少美学上的新鲜感或者提供多少智力上的游戏感,而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回应了现实中的真问题。
与此同时,她是嫁接“道理”和“感受”的高手,很像一个潜伏到武术队的厨子,在习得武林秘笈后,用烹饪大法讲述一招一式,让墙外的吃货们拼命点头:我们懂你。
而对于人生这桩事儿,她的文字通常没有正确的提示,而是像一个诚恳的病友,深深咂摸其中的残酷,在绝望之后,找到自由。
见到刘瑜时,想到一个句子:一个人,浩浩荡荡地,走着。——当然,不是指她有孕在身,体态浩荡。事实上,即便怀孕九个月在身,她也比照片上更为娇小和柔和——而不久前,她也已经完成“升级”,成为一个双鱼座姑娘的母亲。那种浩荡,更多是指这些年来,她作为独立个体,借助文字,所传递出的力量。这种力量,一方面呈现于公共生活中,一方面则体现在她追索爱与自由的过程中,在灵魂层面的负重上。
最近,她有新书《观念的水位》推出,是她近些年专栏和随笔的结集。在谈及让这些文字完成“小团圆”的初衷时,她提到:我相信这些文章结集在一起所传递的信息,相比它们零散的存在,其重量和清晰度是不一样的,而这些信息在今天的中国值得被反复和清晰地传递。而如果对这些信息进行总结,她认为是:既需要对国家之顽固、也需要对普通人之麻木,乃至知识分子之骄矜说“不”。
智识活动上的劳模
刘瑜可以算智识活动上的劳模。这起自她澎湃的好奇心。当她发现一件事儿没有标准答案,而是有许多种答案时,这种不确定性对她来说,是个愉快的事儿,因为这意味着挑战和知识上的开放性。对于接受应试教育过来的中国学生,这是一种稀缺的特质。在她看来,很多极端的结论,譬如种族主义以及头脑中的各种挡箭牌、替罪羊,不过是一种过于懒惰的世界观。所以,当很多人习惯于在思维上“偷工减料”,“多快好省”地得出“豆腐渣”结论时,她却有“丁是丁,卯是卯”的安全施工的自觉。写专栏,对于她是“鸭梨山大”的事儿:每次交稿前焦虑三天,酝酿两天,动笔一天,每挣1000块稿费平均要给自己买零食、咖啡、衣服、化妆品等1200元。
她的文字,在客观层面承担着启蒙的价值,但启蒙这个词却让她有某种伦理上的尴尬,她觉得所谓的启蒙,与其说是教育,不如说是对蒙蔽理性的擦拭。任何人,你只能告诉他不知道自己知道的道理,“你无法叫醒任何一个装睡的人”。
表达上的平民范儿
刘瑜是纯正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学历豪华,却没有之乎者也的腔调。她很少让文章穿着登高鞋或者装扮成圣诞树出来,在她看来,一个道理的意义不在于它能创造多少美学上的新鲜感或者提供多少智力上的游戏感,而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回应了现实中的真问题。她觉得表达观点时,尊重对方的思维方式去讲述,完成有效沟通,比一种自我陶醉的姿态要更为重要。
她对姿态有着特别的反感。当初离开微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害怕一个事情出来,她必须按照一个方向发言,这种表态、站队的压力,让她无从适应,所以,她退出微博,选择去了“冰岛”。在一篇文章里,她解释了冰岛的概念:漂浮着他人的眼光的生活是多么的油腻啊,我所说的冰岛,就是干净而已。
努力坚持“外婆都懂”的常识感的自觉,对老实、朴素的学风和文风的认可,以及建于凡常生活经验之上的诚实治学,使得她的文章逻辑清晰,深入浅出,亲切好读。《民主的细节》大卖,追其缘由,她的看法是:不过是大家口渴了,而我来卖水。
在新书中,一篇《今天你施密特了吗》的文里,她把施密特比作中国思想界的新款LV包,认为在中国这种自由讨论仍然不充分的情境下谈论自由的限度,谈论施密特,就如同一个300斤的胖子,刚减肥30斤,理论家就开始担心:他会不会太瘦。而对于言必称施密特的粉丝们,她有个非常诚恳的建议:其实,从朝阳区到海淀区,可以不绕道阿尔卑斯山,坐地铁10号线就可以。
嫁接“道理”和“感受”的高手
她是嫁接“道理”和“感受”的高手,很像一个潜伏到武术队的厨子,在习得武林秘笈后,用烹饪大法讲述一招一式,让墙外的吃货们拼命点头:我们懂你。这种活泼俏皮的文风,有助于很多人消除对于政治的冷感。政治不是教科书上的“面目可憎”的无用说教,也非权术、阴谋和诡计,它是切实可感的日常生活之所需,是关系到我们是否可以自由选择工作和生活的大问题。
这种嫁接能力的娴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的文青经历。在她出版《民主的细节》《送你一颗子弹》之前,她已写作了小说《孤独得像一颗星球》《那么,爱呢》《烟花》。在那些早期作品中,她就已开始密集使用绝妙而精当的比喻或通感。和她的一些影评、时评写作一样,她的情感小说,也表现出哲学化倾向。
她非常善于从一堆“生活”的道具里,拎出“哲学”的骨架。她对于人的存在状态异常敏感:人生的种种可能性与局限性;爱情,即便本该那么美好的东西,依然是对人的怯懦、渺小和贪婪的暴露,甚至拯救不了;即便,科技让人的选择有了表面上的无限性,可人性中的局限还是无法被改变。在梳理这三本小说时,她发现自己有一个情绪轨迹,即从忧伤到怨恨,再到绝望。对于人生这桩事儿,她的文字通常没有正确的提示,而是像一个诚恳的病友,深深咂摸其中的残酷,在绝望之后,找到自由。
在网上,她有一篇名为《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的文章,流传甚广。文中,她说:“自己终究是幸运的,不仅仅因为那些外在的所得,而且因为我还挺结实的。总是被打得七零八落,但总还能在上帝他老人家数到”九“之前重新站起来,再看到眼前那个大海时,还是一样兴奋,欢天喜地地跳进去。”
面对新出生的孩子,刘瑜希望她个性爽朗,而所谓的爽朗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吧。
【对话刘瑜】
1 公共事物与公共言论
我觉得在中国当下,最缺乏的是用论据和逻辑来朴素地说理,并且以真诚交流为目的的公共言说方式。
新京报:《观念的水位》在强调观念的力量,从《民主的细节》到它,你是否观察到了一些观念的变化?
刘瑜:从《民主的细节》到《观念的水位》中间大约只有三四年,三四年可能还不是一个足够长的审视变化的时间段,但如果放大到近二十年,一些观念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譬如上世纪90年代初,很多民企的目标还只是合法化的存在,但是现在会追求与国企的平等地位,会追问为什么四万亿只投给国企?为什么地王都是国企?为什么民企贷款这么难?又比如人大代表申纪兰,她当了几十年的人大代表,并且自豪地宣传从未投过反对票,以前人们没觉得这有什么,没准还觉得一切对政府言听计从是个好代表的表现,但是最近几年,网上对她的批评铺天盖地。
再比如化工厂,以前政府在哪建化工厂什么时候跟民众商量过?民众为此严重抗议过吗?但是你看这几年,有多少抵制家门口建化工厂的邻避运动?……
诸如此类,都是权利和参与意识在增强的表现。因为一定的制度对应一定的观念基础,当制度和观念错位时,制度是不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制度变革的文化基础正在慢慢形成。
新京报:在书中,谈及知识界存在很多“印象主义”,缺乏实证精神时,有段话是,今天的知识界,放眼望去,一堆人在玩前现代,另一堆人在玩后现代,独独中间那一望无际的空地上,仍然人迹罕至。为什么这么说?
刘瑜:这是因为我觉得一些知识分子的言论在引领一个有害的学风,甚至有害的社会发展方向。我文章里提到的“前现代”,是指一些人以复古为价值导向,尽管从传统中吸收好的资源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些人公开表示要通过儒教原则来设计中国的宪政结构和政治制度,这就有些不可思议。尽管你可以说理论是好理论,历史上被实践坏了,但是如果一个东西曾拥有很多机会被实践,却在绝大多数时候被实践歪的话,是否也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有问题的?
另一个“后现代”的倾向,是指一些学者受到一些故弄玄虚的理论的诱惑,敌视自由、民主等启蒙观念,敌视现代化进程,敌视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这些人往往问题感错位,学风上把引用当做论证,而且似乎引得越玄乎越高级。有意思的是,前现代和后现代现在有殊途同归的合流之势。
我觉得在中国当下,最缺乏的是用论据和逻辑来朴素地说理,并且以真诚交流为目的的公共言说方式。可能在很多人看来,老老实实讲道理是没有吸引力的,他们觉得这是受“美式”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毒害,反而故弄玄虚的学风会受追捧。
新京报:学者熊培云说:在许多公共讨论中,道德被污名化。坚守底线的人被嘲笑,理性克制被认为是“抢占道德制高地”。事实上这个时代最流行的不是抢占道德高地,而是抢占道德洼地,然后一起审判崇高。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刘瑜:我的理解是,在中国存在一种现象,就是在公共领域,什么都不说都不做的人活得最自在自得,既然无所作为,当然很“清白”,又因为这种“清白”,他们常常对有所作为的人横加指责吹毛求疵。就是说,说点话做点事的人会被按照圣人要求——这个人在道德上要完美,在知识上要毫无漏洞,甚至说话的姿态都要完美无缺。
所以在当下,如果你说话做事无底线,即使无比丑陋,也会被很多人夸为真性情,而如果你关心公益和社会责任,就会被怀疑是伪君子。这就是所谓的“抢占道德洼地去审判崇高”吧。这种观念的流传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因为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社会很难形成善的循环和传播,很多人不是没有财力和善意去做好事,而是怕搅入一摊浑水。
2 公共知识分子及其污名化
公知是指具有一定专业知识或文化艺术背景,一定社会影响力,并对公共事务发言的一群人。在中国,什么都不说都不做的人活得最自在自得,无所作为,又常常对有所作为的人横加指责吹毛求疵。
新京报:怎么看“公知”这个概念以及它的污名化过程?
刘瑜:我的理解,从传统意义上讲,公知是指具有一定专业知识或文化艺术背景,一定社会影响力,并对公共事务发言的一群人。但这个词在现实的运用中,已经彻底乱套了。一些人明明不是公知,仅仅是出于公民责任心就一些公共事务发过声,就被视为公知;而一些人明明是传统意义上的公知,仅仅为了打击异己,却否认自己是公知。
公知污名化的原因可能有好几方面。一个原因出在公知自身身上,可能有些公知说话不是特别严谨,特别是对不同意见表现出暴戾之气,这些确实存在。我想如果批评是立足于此,敦促公知在说话时更严谨,更温和理性,这种批评未必是坏事。但有些人对公知的攻击却似乎并不立足于此,他们似乎只是反感一切对政府、对现实的批判性言论,反感有影响力的人对公共事务说三道四。所以我看到的对“公知”攻击最凶猛的,往往是表面上看是批评公知,其实不过是借着批评公知来党同伐异而已。表面上他们主张知识分子应该回到书斋、明星回到演艺圈、商人回到商界,大家都不要“越界发言”,但实际上他们自己对公共事务的发言一点也不少,只是立场不同而已。
公知污名化现象刚出现的时候,我有所担心,倒不是担心个人声誉什么的,而是担心很多人因为这种污名化而不敢再就公共事务发言。但后来我发现在所谓的“污名化”之后,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还在发挥社会功能,而且是很正面的功能——针对很多热点的公共事件,比如任建宇劳教案,比如乌坎事件,比如什坊事件等,所谓的公知群体还是在通过他们的行动或转发、或讨论,将之提到公众关注的视野范围内,可以说,他们还在起着设定公共议题,引导公众讨论的作用。如果这个群体的这个社会功能依然存在,我想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新京报:因为韩寒代笔事件,劈柴等事件的发生,有人说,他们被拉下了“神坛”,现在也进入了偶像的黄昏时代,你怎么看?
刘瑜:大众媒体时代是一个人与人越来越丧失距离感的时代,距离产生美变得很困难,公众人物脸上有几个青春痘,几颗麻子,公众都能看得很清楚。哪怕马丁·路德金,他的抄袭案如果是在微博时代被打假人士纠出来,可能就是另一个唐骏。这是大众媒体时代的特征,中外都一样。这也未必是坏事,神化一个人本身就有问题,偶像思维往往是极权政治的文化基础。
不过把对韩寒柴静之类的批评称作“拉下神坛”似乎不妥,至少在我眼中,他们从来就没有在“神坛”上,不排除个别粉丝将他们视为“神”,但我所了解的绝大多数欣赏他们的人,也没觉得他们品德完美、才华盖世,只是对他们的言行和社会角色抱有大体肯定的态度而已。现在有些人以“拉下神坛”的名义把人说得一无是处,有点大战风车的阵势。一个人只能要么完美无缺、要么一文不值吗?这种非黑即白观是我不能理解的。
3 关于刘瑜及刘瑜的写作
到我现在这个年龄,我对文字不是那么看重了,更在乎道理本身是否有说服力,像秦晖、陈志武老师的东西,文采并不突出,甚至有点干巴巴,但逻辑紧凑,有道理,这就够了。
新京报:作为前文艺青年,怎么看文艺青年这个词?
刘瑜:“文艺”在我看来,就是讲究生活质量,这没什么不好。一个人对生活质量有要求,除了温饱还追求精致,喝咖啡的时候上面打点奶泡,写PPT之外还读点诗,上班下班之外还上下豆瓣,这有什么不好?这个词引起一些人的反感,可能是因为一些人本末倒置,过分追求生活的姿态而显得做作,这种人也许有,但我看也没那么多。
新京报:是否有自己的文字英雄?
刘瑜:和很多人一样,大学的时候很喜欢王小波,喜欢他文字中的举重若轻,没有八股气,也没有痞气匪气,让人觉得很舒服,毫无压迫感。不过到我现在这个年龄,我对文字不是那么看重了,更在乎道理本身是否有说服力,像秦晖、陈志武老师的东西,文采并不突出,甚至有点干巴巴,但逻辑紧凑,有道理,这就够了。
新京报:人性中的哪些弱点是你很痛恨的?
刘瑜:如果一个人把愚蠢和恶毒结合起来,对我来说是难以忍受的。我也很受不了那种什么事儿也不做,但是对做事的人吹毛求疵的人。就像一个站在山脚下的人,对爬到半山腰的人说:你有本事怎么不爬到山顶去?这也是我厌恶的。
新京报:那你自己的个性中,是否有些自己想去克服的部分?
刘瑜:说实话,我是一个比较脆弱的人,我希望能克服掉自己的脆弱。不过某种意义上,可能我对人的同情心、同理心恰恰来自于这种脆弱,但我又不想克服掉自己的同情心同理心,这是一个矛盾。我选择和网络保持距离也和这个有关系,被一些人恶意攻击会很影响我的情绪,但情绪低落本身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情绪低落会影响我的工作状态和思想重心,这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当初退出微博一定程度上是出于自我保护,但与其说是保护自己的情绪,倒不如说是保护自己人生的方向感——我不希望因为网络上的一些个人恩怨而影响了自己“该干吗干吗”的状态。
新京报:会担心孩子的教育吗?
刘瑜:没有特别担心。我觉得孩子来到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其实也挺好的,否则她的人生体验该多匮乏。有时候我想想自己的经历,跨了很多时间空间文化,从小县城到纽约,挺丰富的,我希望我的孩子也有机会体会丰富的人生。
我会告诉她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阶段,也经历过各种厌世,不要为此惊慌,更不要因为这种厌世的“高度”而自恋。如果她因此自暴自弃,我会问她,人生充满了意外,你难道对你未来人生的各种意外不感到好奇吗?
我不会要求孩子一定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佼佼者,但也不希望她因为缺乏任何技能和特长而在小朋友群体中被鄙视,毕竟孩子还是很在乎“同类压力”的。关于孩子,我有个朋友说过,一定要坚定信念,相信自己的孩子最终会长成一个普通人。我觉得这种心态挺好。
采写 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