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以海德格尔的一句‘一切实践传统都已经瓦解完了’为嚆矢。滥觞于家庭与社会传统的期望正失去它们的借鉴意义。但面对看似无垠的未来天空,我想循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的生活好过过早地振翮。
我们怀揣热忱的灵魂天然被赋予对超越性的追求,不屑于古旧坐标的约束,钟情于在别处的芬芳。但当这种期望流于对过去观念不假思索的批判,乃至走向虚无与达达主义时,便值得警惕了。与秩序的落差、错位向来不能为越矩的行为张本。而纵然我们已有翔实的蓝图,仍不能自持已在浪潮之巅立下了自己的沉锚。”
——《生活在树上》,浙江某考生
8月2日,浙江外国语学院主管、主办的教育类报刊《教学月刊》杂志社,通过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题为《生活在树上》的作文。文中表示,上述作文是今年浙江高考的满分作文,且是一篇第一位阅卷老师只给了39分,后两位阅卷老师给出55分高分,最终被作文审查组判为满分的作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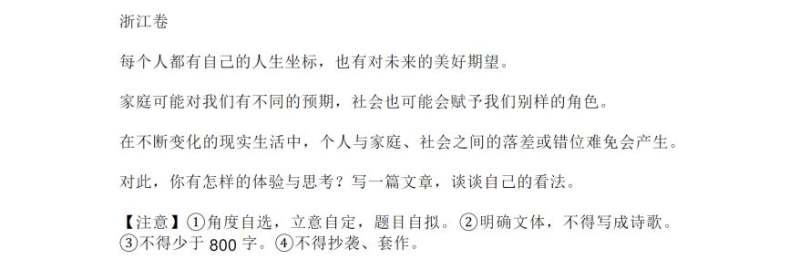
2020年浙江卷高考作文题目截图。
这篇满分作文发布后,引来了诸多争议。反对者最多,比如认为该文用词晦涩难懂,堆砌概念,有故作卖弄、炫技之嫌,乃至斥责该文佶屈聱牙、不说人话。为此还不怕麻烦地罗列了其中的生僻词语,少见的用法,陌生人名和极少出现在大众视野的术语,嚆(hāo)矢、肯綮(qìng)、玉墀(chí)……滥觞、祓魅、赋魅、婞直……海德格尔、卡尔维诺、麦金太尔、柯希莫、韦伯、维特根斯坦……达达主义、符号客体、知性的傲慢、实践场域的分野等,认为这些“不明觉厉”的字词,将这篇文章“粉饰成进阶版的八股文”,以行文的“高级感”博得了阅卷老师的激赏。
支持的声音也不少,认为其旁征博引,逻辑严谨,说理到位,展现了极为深厚的阅读功底。而作为浙江省高考作文阅卷大组组长的陈建新,在对该满分作文点评称,该文“老到和晦涩同在,思维的深刻与稳当俱备。”陈建新说:“它的每一句话都围绕着个人的人生理想和家庭社会的期待之间的落差和错位论说,文章从头到尾逻辑严谨,说理到位,没有多余的废话,所有的引证也并非为了充门面或填充字数。”
截至目前,《教学月刊》已将该篇文章删除。据其他媒体报道,《教学月刊》杂志社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删除前述微信文章,是因为浙江省高考招生工作仍在进行中,现在发布可能不是很合适。”但争议并未随着文章的删除而消失,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争论的焦点,也从该篇文章是否担得起高考满分示范作文之名,变成了对高考作文评分标准是否存在偏差,中学作文教育指挥棒应偏向何方,以及对考试作文与作文教育,学生写作习惯与思维方式的全民探讨。

网友评论截图。
当写作文的目的是为了升学考试之时,我们应该如何写出一篇好作文?对此,文学家王鼎钧写下了“作文四书”,而其中的《讲理》从作文课开始,通过教师和学生的互动,层层推进,给出议论文写作的关键步骤:建立是非论断的骨架——为论断找到有力的证据——配合启发思想的小故事、权威的话、诗句,必要的时候使用描写、比喻,偶尔用反问和感叹的语气等。他的著述使议论文写作有章可循,为研习者提供路标。

《讲理》,王鼎钧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10月版。
王鼎钧说,为什么同学们见了论说题作不出文章来呢?也许因为家庭和学校都不喜欢孩子们提出意见,只鼓励他们接受大人的意见,也许论断的能力要随着年龄增长,而他们还小。那么,该怎么办呢?王鼎钧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我站出来告诉那些小弟弟小妹妹,你们的生活中有感动,所以可以写抒情文;你们的生活中有经历,所以可以写记叙文;你们的生活中也产生意见,一定可以写论说文。”
为创作《讲理》一书,王鼎钧专门做了一年中学教员。他说,“教人写作一向主张自然流露,有些故事说作家是在半自动状态下手不停挥,我想那是指感性的文章。”议论文应该怎么办呢?王鼎钧说,“论说文(即议论文,下同),并没有那样神秘:它像盖房子一样,可以事先设计;它像数学一样,可以步步推演。你可以先有一个核,让它变成水果。”
“作文这堂课固然可以培养文学兴趣,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帮助学生通过考试,顺利升学,这两个目标并不一致,当年考试领导教学,在课堂上,老师可能太注重升学的需要,把学生的文学兴趣牺牲了。”考试作文与作文教育无法在异中求同吗?在另一本《作文七巧》中,王鼎钧说:“作文课的两个目标固然是同中有异,但是也异中有同,文学兴趣是什么?它是中国的文字可爱,中国的语言可爱,用中国语文表现思想感情,它的成品也很可爱,这种可爱的能力可以使作文写得更好,更好的作文能增加考场的胜算。”

《作文七巧》,王鼎钧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10月版。
以下内容节选自王鼎钧所著的“作文四书”系列之《讲理》《作文十九问》,由出版社授权刊发。正文中的“杨老师”是作者王鼎钧笔下的主人公,语文老师杨书质。作者通过描写“杨老师”与“吴强”等几位学生的交流来讲作文。
原文作者丨王鼎钧
摘编丨何安安
有标准,才可以言之成理
杨先生不免自问,我教他们写论说文,他们除了在升学考试时多一些胜算,还有什么收获?在这学期即将结束,离情别绪升起的时候,杨先生想到一句话:“人生就是不断地离别。”离别的前面必然有相逢,有交往,否则哪里来的离别?这句话可以稍稍修改,“人生就是不断地聚散”,或者“人生就是不断地握手与挥手”。有人对离别的感受特别深刻,情绪压倒了、淹没了一切,这才说人生就是不断地离别,这句话是抒情文,不是论说文。
杨先生自己检讨,这一年,他很注重论说的方法,他也想到,论说文的内容需要有是非标准。平时寒暄的时候,人和人之间似乎没有歧见,可是,一旦面对比较突出的问题,那就无可避免地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即使是父子兄弟之间,也不见得能意见一致。
人是复杂的动物,对同一件“事实”,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对同一事实的价值,有彼此不同的评判。这是因为,各人有各人的是非标准。“标准”是深藏在他心里的一把尺、一块试金石。他拿外面发生的事实,向这块试金石上磨一磨,用这把无形的尺量一量,然后他说,这件事是对的,是不对的,说它的价值很大或价值很小。评判是非固然要弄清外面发生的事实,尤其要在内心建立一个标准,没有标准就不能判断。各人意见不同,是由于各人内心的“标准”不尽相同。
这样看来,“标准”太重要了,有标准,才可以言之成理;没有标准,免不了要彷徨困惑。几个人标准相同,谓之志同道合,否则“道不同不相为谋”。没有标准就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怎能写论说文?错误的标准,产生错误的意见,又怎能写出一篇站得住的论说文?就文章的形成来说,先有标准;就学习的过程来说,可靠的标准往往到最后才建立。教人写论说文,应该先助人建立标准。可是,标准的建立,绝不是一门功课、一个教师所能独力完成的。追究到这一层,真觉得兹事体大。
建筑这个“标准”的材料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知识。
如果有人对我们说,今天月球上投票选举总统,我们立刻可以断定这是胡说,因为根据我们现有的科学知识,月球上不可能有“大选”。科学知识是我们胸中的标准,凭着它,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香灰不能治病,照相机不会摄去人的魂魄。知识产生判断是非的能力,知识愈正确,判断愈可靠。
除了知识,还有理想。
很多人,尤其是社会改革家,往往先悬一个理想,朝这个理想努力,在他的心目中,人与事的是非,要看跟他的理想配合还是冲突。“每一个清寒的学生都该免缴学杂费”是一种理想,现在各学校的收费办法不符合这理想,抱有这种理想的人,就要批评现行的收费办法不对。“学校要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这是教育家的理想,所以他们反对投机取巧的“升学主义”。
除了理想,还有约定。例如中国人讲信义,信义就是一种约定,你不欺骗我,我也不欺骗你,我做事对得起你,你做事也对得起我。宗教的教规也是一种约定,例如初一十五上香,例如星期天做礼拜。我们俗人可以吃肉,如果和尚吃肉,我们会说他错了,关系在有没有约定。
理想可以变成知识。当法国还在国王和贵族手中的时候,《民约论》里面的那些主张只是对法国前途的理想,到后来,它变成政治常识。知识也可以变成一个人的理想,一个青年,在有了太空方面的知识以后,可能主张努力发展太空科学。
约定可以变成知识,“欠债还钱”本是一种约定,到今天,债权问题是相当复杂的法律知识。知识有时也变成约定,有关公共卫生的许多“约定”,大半是知识普及以后变成的。约定,有时候实在是一种理想。例如各种的誓词、公约之类,没有人能完全做到,它是一个人或一个团体的理想,披上了约定的外衣出现。在这种情形下,理想很容易产生“约定”。
知识可能跟约定抵触。想当年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里来,再三拜托导师说:“孩子如果不用功,请您尽管打。”导师果然动手打,孩子果然乖乖地用功,可是,“知识”告诉我们,这是不好的。
约定往往与理想抵触。男女结婚要摆酒席,雇乐队,铺红毡,放鞭炮,这是“约定”。很多人在未结婚前有一个“理想”,希望自己的婚礼能简化革新,不落俗套,可是事到临头,挣不脱社会习俗的约束。
少谈“标准”,多谈方法
杨先生把知识、约定、个人理想三者的关系排列起来,写在一张卡片上,不禁想起自己的许多往事。
他想起,人本来是浑浑噩噩的,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有是非。长大以后,人生多半有一个时期觉得苦闷、迷惑,内心有剧烈的冲突,觉得不容易判定是非。再过若干年,这个人成熟了,定型了,他有了自己的见解,达到“不惑”的境界。这是思想发育的过程。在那些成长发育的日子里,人不断地吸收知识,发现约定,编织理想,这三样东西日夜在心中,相生相克,加减乘除,最后得到平衡,这时,他也就得到了判断是非的标准。

电视剧《清平乐》剧照。苏轼、苏辙赶考。
人的个性、气质不一样,历史、环境不一样,所吸收的知识、所接触的约定不一样,个人的理想不一样,知识、约定、理想三者,在每个人内心加减乘除的计算式又不一样,结果产生了几千几万个是非标准。以打牌而论,有人认为打牌绝对是错的,有人认为打牌是正当娱乐。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
豪赌是错的,打小牌是对的。
通宵恋战是错的,只打八圈是对的。
与赌徒聚赌是错的,跟好朋友逢场作戏是对的。
只要不瞒着太太,打牌不算坏事。
只要能维持好的牌品,打牌不算坏事。
只要常赢钱,打牌就不是坏事。
只要不动用子女教育费做赌本,打牌不是坏事。
几乎每个人都想扩大使用自己的标准,希望别人依从他的判断。同时,几乎每个人,标准一旦在内心形成,就很不容易改换。所以,人与人很容易发生争执。论说文,不论写得多么含蓄,它无可避免地要伸张自己的标准,削弱另一些人的标准。这就是所谓“论说文的战斗性”。
可是“战斗性”这样的字眼太容易使人误解了。认为自己的标准是唯一的标准,是至善的标准,写起文章来声色俱厉,奋不顾身,那会变成一个暴戾的论客……“我想得太远了。”杨先生从冥想中醒过来。他不能在黑板上抄几句话,说“这是标准”。他不能印一份讲义,说“这是标准”。他也不能介绍一本书,说“这是标准”。他只能尽量把好的东西告诉他们,把有启发性的事物指给他们看,任他们的心灵自己去组合去分解,去发生秘密的震动。到最后,他还是决定少谈“标准”,多谈方法。
熟悉方法,遵守方法,最后使自己的作品成为那方法的化身
可是,有人说,写文章是没有方法的。真奇怪,这人写文章,明明这里用了古人用过的方法,那里用了今人用过的方法。世上万事皆有方法。记否?我们小时候学习怎样用筷子,连那样简单的事都有方法。记否?我们学习怎样用毛笔写字,这事我们得学一辈子,用笔有笔法,用墨有墨法,有时候还用水,有水法。从来没有一个音乐家说过,拉提琴没有方法,你只要拿起琴来拉;从来没有一个书法家说过,写字没有方法,你只要拿起笔来写。唯独到了写文章,怎么就没有方法了!
文章,无论如何是人用大脑指挥手做出来的,在制作过程中,一定经过有意的安排,这种安排,应该可以重复使用,互相观摩。就算“文章天成”吧,“天”也有方法,天下雨是有方法的,人发现了这方法,已经可以造雨;地生钻是有方法的,人发现了这方法,可以人造钻。杨先生相信,作家对他所使用的方法不能保守秘密,他必须写文章,他必须发表他的文章,文章发表出来,他的写作技巧就暴露在我们眼前,我们花心思研究许多作家的文章,可以找出他们的方法来。
另外有人说,单凭方法不能产生杰出的作品,好,这句话总算承认有方法了,问题在作品的档次高低。“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这种作品当然杰出,然后,有些作品光芒千丈,有些作品光芒百丈,有些作品斗室烛光,有些作品,例如我们写的论说文,好比一只萤火虫。如果档次越低越依赖方法,我们正是需要方法的人,方法正好对我们这些人有用。有些萤火可以变成烛光,有些烛光可以变成星光,有些星光可以变成月光,有些月光会不会变成日光?如果真有不需要方法的作家,那也可能从依赖方法的作家中蜕变跃升。
李白杜甫都是唐朝的诗人,唐人作诗要遵守韵律,规矩很多,李杜的光芒万丈不像是从没有方法产生,很可能是由遵守方法开始。《全唐诗》搜集两千多个诗人的四万八千多首诗,这些诗人写诗都用同样的方法,后人精选七十七人的作品辑成《唐诗三百首》,这七十多个人好像成了唐诗的代表。看样子并不是没有方法才会产生杰出的作品,而是诗人熟悉方法,遵守方法,最后使自己的作品成为那方法的化身。可以说方法给作家共同的基础,作家个人在上面建立独特的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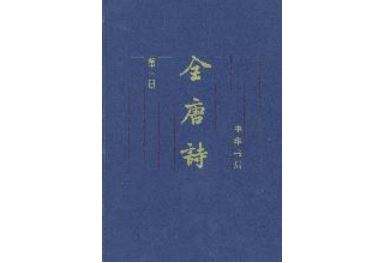
《全唐诗 : 增订本》,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书局2008年2月版。
附:《作文十九问》之第十六 如何增加词汇
问:增加词汇似乎不一定增加生字?
答:原则上识字越多词汇越丰富,但是并非增加多少词汇就增加多少生字。李白又叫太白,又叫青莲,这些字你都认识,都是用熟字组合起来的。太白又叫谪仙,也许这个“谪”字你很生疏,这才增加一个生字。
夏丏尊先生说过,一个意念可以有许多符号。今,目下,眼前,现在,当代,现代,斯世,并世,我们的时代,这个年头,是一个意念;滥觞,渊源,开端,起源,发生,发端,发轫,开头,开始,开创,开场,揭开序幕,第一步,破题儿,行剪彩礼,是一个意念。
问:这些意念相同的词,是不是可以随便换用?
答:这可就一言难尽了。“今”是单词,“当代”是复词,一句之中若有好几个词,通常不能都用单词,也不宜都用复词,多半是奇偶相错。“开头”是白话,“滥觞”是文言,该用哪一个,得看文章的风格和句子要达成的效果。此外还得考虑到字音,也就是音节。还得考虑一句之内用字不能重复。我说不周全,说全了你也记不住,记住了也不能照着方子用。
问:那怎么办?
答:多读。读破万卷,神而明之,都说这个老办法不科学,到了这个“非科学”的层面,还得用这个不科学的方法。
多读好文章,看人家在要紧的地方反复说一个意思,反复而不重复。看文章怎样才会读着顺口,看着顺眼。看人家长短疏密安排得多么妥当。

《作文十九问》,王鼎钧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10月版。
问:我手上要有多少词才够格?
答:这个问题很难答复,坦白地说,我不知道。不过我想起一个故事。有个皇帝问他的大臣认得多少字,那人回答:“臣识字不多,用字不错。”
问:从前的进士翰林,熟读经史,还说自己识字不多,太客气了。
答:这个答案很出名。回皇上的话,不能不客气。那个大臣如果夸耀渊博,万一被皇帝当场考倒了,后果一定严重。可是对着皇上,你一味谦虚也不行,你得表示你不是白吃瞎混的人,你有资格在金銮殿上排班,所以下面紧接一句“用字不错”。这个答案可以说不亢不卑。
问:识字不多,用字不错,我也几乎做得到啊!
答:他们“明训诂”的人,对识字、用字的要求很严。从前有个秀才想越过一条水沟,不知道怎么做才好,他那副为难的样子引起一个农夫的注意,农夫对他说:“你可以跳过去啊。”秀才听了,站在水沟旁边,两脚并拢,向前一纵,扑通落到水里去了。农夫说:“你错了,看我的!”农夫后退几步,向前猛冲,右脚先踏上对岸,左脚紧跟过去。秀才纠正他:“你才错了哪,你这是跃,哪儿是跳?”
问:这恐怕是挖苦书呆子的吧?
答: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看这个故事。打开古色古香的字典看看,“跳”和“跃”确有分别。你如果在“小学”的训练里浸润过,你也可能认为跳跃不分是用错了字,甚至可以说是不认识这两个字。当年中国文化界有文言白话论战,文言一派就有人说写白话文的人不识字。
问:不识字?不识字?
答:就拿白话文的招牌字“的呢啊吗”来说,“的”本来是白色,“呢”是说悄悄话,“吗”就是“骂”。
问:哦,那个大臣说自己“用字不错”固然是肯定了自己,说“识字不多”也很有斤两啊。
答:所谓用字不错还有一层意思。王安石的“春风又到江南岸”改成“春风又绿江南岸”,没改以前是“庸句”,改了以后是名句,你也可以说“绿”字用对了,“到”字用错了。
问:人家告诉我,要把白话文写好,得先把文言文学好。(答:也有人这样告诉我。)可是又有一种说法完全相反:你看,某某人的文章半生不熟,都是文言害的。(答:这个说法,我也听过。)我到底该听谁的?
答:这要看你是为了升学呢,为了实用呢,还是为了当大作家。如果当大作家,不但要学文言文,还要学外国文呢,还可能要去提炼方言呢。升学考试的测验题,有一半是从文言文里头找出来的。升学考试的作文题,像“仁与恕相互为用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也得文言有根底才下得了笔。
问:若是只求实用,又怎么说?
答:先给“实用”下个定义:不为升学考试,也不为了当大作家,平时喜欢写写,表情达意,自得其乐,这样的人可以不读文言典籍。在七十年八十年前,这样的人是写不好的,因为那时候白话文学还不成熟,得向文言典籍借火取经。现在的情势不同了,用白话写成的作品有这么多,有这么好,文言文的式样手法,文言文的哲理玄思,大都藏在里面、化在里面,开启了从白话文学作品学习白话文学写作的时代。
本文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授权节选自王鼎钧“作文四书”系列之《讲理》《作文十九问》。摘编有删节,标题由编者所加。
作者丨王鼎钧
摘编丨何安安
编辑丨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丨李世辉











